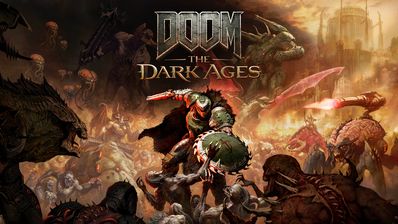我爲“毀滅戰士”續作的名號而來,最後卻折服於“黑暗時代”本身
即使是在五年後的今天,我也依然會向所有我認識或不認識的遊戲玩家,推薦《毀滅戰士永恆》(以下簡稱“永恆”)——雖說“毀滅戰士”這四個字本身已經如雷貫耳,但“永恆”有的可不僅僅是“繼承家業”式的虛名。
有着大量思考餘地的立體戰鬥、不間斷湧現的各類抉擇點,乃至最爲淺嘗輒止的玩法都能感受到的“血腥屠戮”快感,都足以讓玩家內心的情緒之海爲之激盪,也讓“永恆”作爲一款FPS遊戲,有了能夠媲美“四大ACT”的高速戰鬥體驗。除了渲染比起前代作品更加偏亮、飽和度偏高,以至於“黑暗恐怖”風味略遜一籌外,我幾乎無法在“永恆”身上挑出其他大毛病來。

不過,一枚硬幣總是有正反兩面的。“永恆”做到了玩法足夠完善自洽,賣相也足夠“現代”。但與此同時,“永恆”的這些優點,也不可避免地爲整個系列的發展帶來了一大問題:重啓之後的“毀滅戰士”系列,似乎已經摸到“高速立體FPS”玩法的天花板了——如果再有續作,它又該去向何方?而如果再悲觀一點的話……有了“永恆”珠玉在前,下一代的“毀滅戰士”,相比之下會走下坡路嗎?
自2024年6月公佈開始,《毀滅戰士:黑暗時代》(以下簡稱“黑暗時代”)就註定了會伴隨着這些或積極或消極的追問。這確實有些不太公平,但也確實是合理的——“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誰叫你姓“毀滅戰士”呢?
好在,這些被拋出的問題並沒有“下落”得太久。在距離“黑暗時代”初次公佈9個月後的今天,關於“遊戲面貌如何”這道題,我們已經得到了“第一問”的具體答案——感謝微軟和貝賽斯達的邀請,我們在這個月的早些時候拜訪了微軟的香港辦事處,並在那裏玩到了“黑暗時代”的最新Demo。

整個試玩活動會場,抓人眼球的地方有不少。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試玩區域裏十幾臺“地獄紅”配色的RGB海景房電腦主機,它們與屏幕上的內容交相輝映,別有一番趣味。除此之外,巨幅主視覺圖裏的Doom Slayer新形象,也非常令人難忘:在“黑暗時代”中,剛剛從亞金人競技場裏打出名堂的Doom Slayer身裹毛皮披風,左手還拿了一面厚重的圓盾,乍一看頗有點隔壁“北歐戰神”的意味,與先前作品中的形象有不小的差異。

我知道你們可能想說什麼——拿着盾防禦的Doom Slayer,看起來似乎一點都不夠“猛男”。其實剛上手遊戲時,我也有着類似的想法——在扛上這塊盾牌後,Doom Slayer不但不再能夠“衝刺”,就連“二段跳”的能力都沒有了。與“永恆”的角色機動性相比,這實在是有點“從奢入簡難”。
但隨着新手教程關卡的結束,密密麻麻的“士兵”和“幼魔”(至少前代裏它們是叫這個名字),開始在你面前釋放一個又一個的巨大彈幕時,你纔會真正意識到手裏這塊厚重圓盾的價值。
今年年初在接受採訪時,“黑暗時代”的設計總監Hugo Martin與執行製作人Marty Stratton曾提到過,在這一代作品裏,他們從老“毀滅戰士”三部曲裏取了不少經,擴大了“地面平移”在跟槍和躲避彈幕這兩大最基本玩法中所佔的比重,從而“另起爐竈”,走了一條與“永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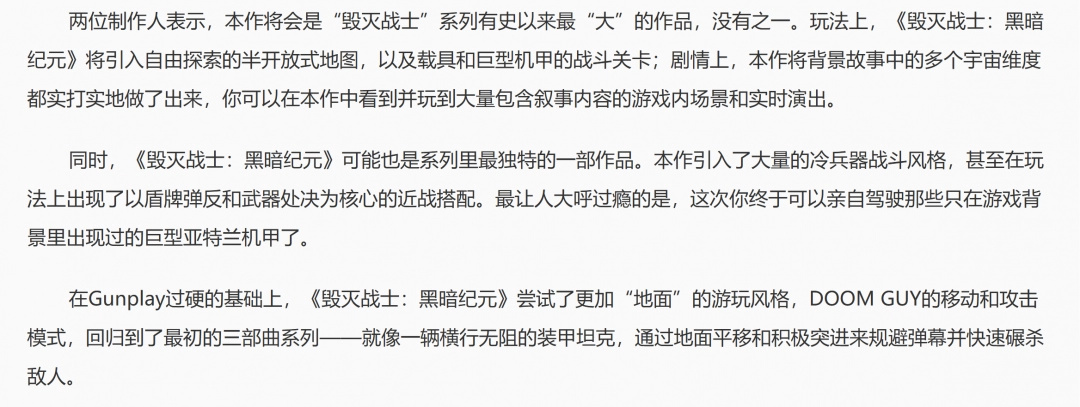
話雖如此,但老“毀滅戰士”三部曲裏逼仄狹窄的場景和屈指可數的敵人布制,在今天肯定是不能再學了。雖然Doom Slayer本身的機動性有些“懷古”,但數量激增的敵人與面積擴容了數倍的地圖場景,又彌補了這一點,讓“黑暗時代”依然呈現出了“毀滅戰士”系列那激情四射,在高難度下甚至可以說是“刀口舔血”的戰鬥體驗。
當體積又大、傷害又高的彈幕從你四面八方襲來時,你真的會很慶幸自己的左手有着這麼一面盾牌,能讓你在嚴峻的戰局下稍作休息,清空一下大腦緩存,並考慮下一步的破局之法。比起“製作團隊的憐憫”,Doom Slayer的這面新盾牌,更像是一種水到渠成的遊戲平衡性安排。

更何況,做出過2016版《毀滅戰士》和《毀滅戰士 永恆》的id Software的創作者們,又是何等人物——他們怎麼可能只給這面盾牌一個簡單的“防禦”能力?當你按下左扳機,舉起盾牌,並發現敵人的身上出現了一個鎖定圓圈時,你自然而然地就會萌生一種“幹大事”的慾望——舉盾觀察固然安逸,但現在我是Doom Slayer,不朝着鎖定方向來一次“盾牌猛衝”,簡直就是對不起我打開這個遊戲的動機。以至於,儘管有時候“盾牌猛衝”並非當前局勢的最優解,但金屬衝擊惡魔血肉的沉悶聲響,還是會讓人控制不住扣動自己的右手食指。
這面盾牌的妙用,遠遠不止這些。除了激進的“盾牌猛衝”和保守的“防禦”外,你還可以選擇一條折中之道,像一個收放自如的戰鬥大師那樣,只在必要時舉起盾牌,算好窗口期,彈走敵人發射的特殊綠色彈幕,讓他們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裏需要插一句:“黑暗時代”的近戰機制把“永恆”裏的“血拳”和普通近戰融合到了一起。在“黑暗時代”裏,即使是普通近戰(以及它在合適條件下觸發的“壯烈擊殺”),也同樣需要蓄力打出。雖然這個設計看似大幅削弱了Doom Slayer的近戰能力,但在盾牌彈反成功後,你就可以立刻獲得一層可用的近戰充能。
也就是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你可以把Doom Slayer的這面盾牌看作是“電鋸”的一種變體——它提供近戰充能,近戰(以及“壯烈擊殺”)則同時提供血量和子彈的雙重補給。雖然繞了一點,但終究是殊途同歸。而且在習慣之後,你會發現這樣的新型資源循環模式,還要更加絲滑流暢一些,也更加符合“黑暗時代”相比於“永恆”,從“躲避生存”到“連殺生存”的基礎戰鬥思路變化。
除了這種抽象概念外,盾牌還有更“電鋸”的部分。或許,你早就已經注意到了宣傳CG裏盾牌上那個拉環的特寫——它會讓你的盾牌變成一枚可投擲的圓鋸,瞬間消滅掉投擲路徑上的所有“炮灰”級敵人,或結實地嵌在一名“重型”敵人的身上,用密密麻麻的鋸齒連續對其打出硬直,讓你有充足的時間將其變成自己雙管霰彈槍下的又一個新亡魂。

而在戰鬥之外,你還可以在關卡地圖中的衆多迷宮裏,感受到這面盾牌的存在感:“盾牌猛衝”可以用來打破脆弱的牆壁,找出新的道路;“投擲”可以驅動數個齒輪齧合在一起的機關,打開原本緊閉的大門;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扔出這枚盾牌還能夠讓你瞬移……當然,我提到這些並不只是爲了說明盾牌另外的一些妙用而已。讓這些妙用發揮作用的衆多地牢迷宮,同樣是“黑暗時代”相比於前代作品,在遊戲內容上所做的又一大提升。
在“黑暗時代”裏,“毀滅戰士”系列裏的線性關卡模式得到了由線至面的擴展,在“努爾”星球表面的衆多地區上(後面大概率還有地獄),你都可以在完成主線任務的過程中,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探索路線,發掘其中的升級資源和收藏品。
與此同時,埋藏着這些資源的衆多迷宮,也體現了Hugo和Marty所試圖繼承的,老“毀滅戰士”三部曲在戰鬥體驗之外的另一面——小範圍的、精緻的迷宮探索和解密體驗。儘管這些謎題看起來有點老掉牙,有的可能還會讓你“卡關”許久,但在成功解出來的那一刻,你也確實會油然而生一種不亞於在地面大殺四方後的成就感。

實際上,除了“戰鬥系統變革”和“地圖探索升級”外,這次的“黑暗時代”試玩,還涉及了更多能夠令人感到興奮的內容。比如,你現在可以親手操控“永恆”裏刷了一大波存在感的“亞特蘭機甲”,用一擊蓄力重拳把同樣是摩天大樓一般高的巨大惡魔打趴在地;再比如,你還可以騎上由兇惡爬獸和光翼拼接而成,散發着極度粗糲與野蠻氣息的“鋼鐵飛龍”,把對抗惡魔的戰火蔓延到“努爾”星球空域中。

除此之外,本作的槍械玩法也同樣經歷了一番革新。在外觀上,Doom Slayer的各種武器多了一絲亞金人的暗黑中世紀風格;而在內容上,衆多槍械的特殊功能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你可能已經猜到,由於有了“盾牌猛擊”,雙管霰彈槍的“肉鉤”已經被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永恆”裏需要主動觸發的噴火器效果,被直接加入了雙管霰彈槍的升級效果中,只要打中就能自動給對面掛上灼燒,使其源源不斷地掉落護甲補給。
當然,我知道你們肯定希望我就這些內容再多聊點什麼——越多越好。但不幸的是,與“亞特蘭機甲”“鋼鐵飛龍”,以及大變後的槍械玩法有關的內容,這次的“黑暗時代”Demo都只是提供了淺嘗輒止程度的試玩。關於這些部分,我只能說一句“未來可期,我也很期待”。

但當我寫到這裏,回憶起自己在通關了“超級暴力”難度的四個試玩關卡後,望着屏幕上的Demo主界面愣神時的心境,我又感覺,自己對“黑暗時代”的情感,好像不只是“期待”這麼簡單。
如果不是前面提到了一次2016版《毀滅戰士》,恐怕我都快要忘了,“毀滅戰士”的系列傳承其實經歷過一次比較長時間的斷檔。而現在操辦着“毀滅戰士”續作事業的,也早已不再是當年的卡馬克、羅梅羅之衆了。在這種“物是人非”的前提下,能夠不靠前作名氣、不靠“改革”噱頭,只是靠純粹的玩法創新,來做系列新作品的遊戲IP,如今已非常難得。
倘若再發散些遐思的話:能夠使人基本忘掉“毀滅戰士”系列的傳承斷檔、使人感受到“毀滅戰士”的核心精神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也說明了id Software的現有製作團隊,實在是不容小覷的一羣人。

從2016版《毀滅戰士》,到“永恆”,再到“黑暗時代”,在這由id Software所製作的“現代‘毀滅戰士’三部曲”裏,“毀滅戰士”作爲遊戲的精神傳承固然重要,但除了令人多巴胺狂飆的血腥暴力戰鬥外,他們也同樣提供了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那是他們與初代“毀滅戰士”團隊跨越時空的對話,也是玩家和“毀滅戰士”這個有着二十多年悠久歷史的遊戲系列,跨越時空的對話——能在本來只被拿來與毛片做類比的“毀滅戰士”裏感受到這些東西,實在讓我有點意外。
或許這是因爲,所謂的“第九藝術”,真的並非只是遊戲廠商們爲了牟利,而生造出來的概念吧。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