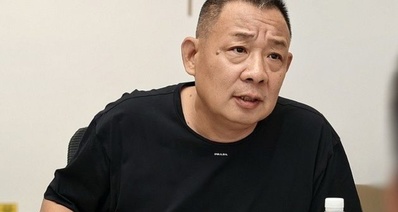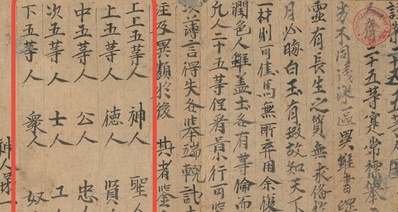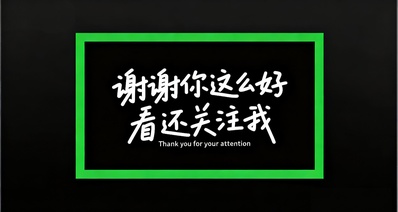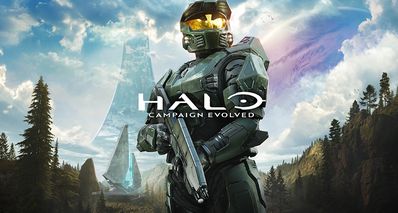秦朝
气候背景:从温暖期到干冷期的转折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秦朝的建立(公元前221年)处于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时期,这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消耗。然而,秦朝末年至汉朝初年,中国气候经历了一个由暖湿向干冷的转折期。这种气候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其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庞大帝国。
尽管秦朝历史短暂,留下的史料有限,但我们仍能从一些文献中窥见其末年天灾的踪迹。
《史记·秦始皇本纪》 虽未直接详尽记载秦末的全国性大旱,但在描述陈胜吴广起义的背景时提到,“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这场“大雨”虽是局部事件,却直接点燃了反秦的导火索。值得注意的是,极端降雨事件也常常是气候异常的表现之一。
虽然直接记载秦末灾害的文献不多,但我们可以从汉初的记录中反推秦末的情况。《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初“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 贾谊在《论积贮疏》中也描绘了汉初“人相食”的惨状。这种大规模的饥荒,除了战争破坏外,往往与之前的农业歉收紧密相关,而农业歉收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
有研究指出,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开始下降。战国时期,苏秦形容关中为“天府”,“田肥美,民殷富”。 但到了东汉,班固在《两都赋》中只能说关中“号为近蜀”,其富庶程度已不及成都平原。这种变化的背后,除了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与气候趋于干旱、水资源减少等环境因素有关。
2002年在湖南里耶出土的大量秦代简牍,为我们了解秦朝的基层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详实资料。 里耶秦简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户籍、田租、赋税、徭役、司法、邮传等方方面面。
简牍中详细记录了军队和官吏的粮食消耗量,以及对土地开垦和农业生产的严格管理。这种精细到极致的管理,一方面体现了秦朝强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其物资储备可能并不宽裕,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脆弱。一旦气候变化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这种高度紧张的社会结构就容易崩溃。
东汉
气候背景:由暖转寒的开端
科学研究表明,从西汉末年开始,中国气候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转折,由相对温暖湿润期转向干冷期。这一转变深刻影响了以农业为本的汉帝国。竺可桢先生在其不朽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便指出,西汉大部分时间处于一个温暖期,但自西汉末年起,气候开始波动并趋于寒冷。这一宏观背景,使得汉代末年的农业生产变得极为脆弱。
西汉的末代皇帝,尤其是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史书中的灾异记载陡然增多,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灾难链条,预示着王朝的危机。
水旱频仍与粮食危机:《汉书·五行志》中充满了西汉末年灾害的记录。例如,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郡国三十余饥,民流离, 就谷关东。” 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关东大水,饥,民相食。” 持续的水旱灾害直接摧毁了农业生产,导致大规模的饥荒和流民潮。
罕见的霜雪与风灾:气候变冷的直接证据便是反常的霜雪天气。《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四月,陨霜,杀屮木,海濒尤甚。”初夏降霜,对农作物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此外,沙尘暴等风灾也异常频繁,《汉书·五行志》描述汉成帝时的一次强沙尘暴:“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着地者黄土尘也。”
地震频发:《汉书》同样记载了多次强烈地震。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郭,杀六千余人。”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 地震不仅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在“天人感应”的时代背景下,严重动摇了人们对皇权稳固的信心。
灾异、谶纬与王莽篡汉
在汉代,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应”学说深入人心,灾异被普遍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失德的警告。西汉末年接连不断的灾难,使得“汉运已衰”的观念弥漫于社会上下。王莽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将自己塑造为顺天应命的“圣人”。
他一方面以儒生的姿态出现,积极救灾,收买人心。据记载,西汉末年饥荒和瘟疫导致“死者以百万数”,而朝廷应对无力。王莽则以大司马的身份建立医疗点,甚至自掏腰包安葬死者,极大地博取了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他与儒生们大肆宣扬符命谶记,将每一次自然灾害都解读为汉室气数已尽、需要“改朝换代”的证据。最终,在天灾不断、人心思变的背景下,王莽以和平禅让的方式,终结了西汉的统治,建立了新朝。可以说,西汉的灭亡,天灾是为其敲响的丧钟,而王莽则是在钟声里登台的野心家。
如果说西汉的灭亡是慢性病,那么东汉的倾覆则更像是一场急性重症,而其病灶同样深植于天灾的温床。
西汉
气候背景:小冰期的严酷考验
现代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东汉末年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小冰期”,气候异常寒冷,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都远超前代。这一时期的灾害记录,在《后汉书·五行志》中更是触目惊心。
瘟疫——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所有天灾中,对东汉末年社会冲击最大的莫过于连年不断的大规模瘟疫。桓、灵二帝时期(公元147-189年)是疾疫的集中爆发期。
史不绝书的疫情:《后汉书·孝桓帝纪》和《孝灵帝纪》明确记载: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京师疾疫”,同年“九江、庐江大疫”;延熹四年(161年),“春正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年),“春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到黄巾起义后的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短短三十余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多达七八次,其惨烈程度可以想见。曹植的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当时社会凋敝的真实写照。
与天灾的恶性循环:瘟疫的爆发往往与水旱、蝗灾等其他灾害相伴相生。例如,熹平六年(177年),“夏四月,大旱”,同年“七州蝗”。大旱导致饥荒,民众易子而食,抵抗力下降,流离失所又加速了疫病的传播。此外,地震、洪水、冰雹等灾害也频繁发生。如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极度的严寒进一步加剧了民间的苦难。
面对连绵不绝的天灾和腐朽不堪、无所作为的朝廷,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陷入了绝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应运而生。
《太平经》作为其核心经典,本身就包含了对现实灾难的解释和对理想“太平”世界的向往。张角以“大贤良师”自居,核心手段便是“符水治病”。在瘟疫横行、求医无门的乱世,张角的太平道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提供了精神慰藉和最基本的医疗救助,因此迅速发展,“十余年间,众数十万,遍于八州”。
当政治黑暗与天灾人祸达到顶点时,张角振臂一呼,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数十万头裹黄巾的饥民与信徒揭竿而起,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它却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并直接导致了地方州牧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局面,汉朝的丧钟就此被彻底敲响。
唐朝
现代气候学研究普遍认为,唐朝的前半期,尤其是盛唐开元、天宝年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被称为“隋唐温暖期”。温暖的气候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关中地区物产丰饶,支持了长安城的繁荣和帝国的对外扩张。杜甫诗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描绘,既是开元盛世的写照,也离不开良好气候的支撑。
晚唐的“小冰期”前奏
然而,以安史之乱(公元755年)为分水岭,唐朝的气候开始发生显著转变,逐步进入一个持续干冷、旱涝灾害交替频发的时期。这一气候转型期,被一些学者视为全球“中世纪温暖期”的结束和“小冰期”的开端。持续的低温和不稳定的降水,使得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高,尤其是在北方地区。
晚唐的史籍,特别是《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五行志”以及《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触目惊心的天灾。
南涝北旱的格局形成:安史之乱后,一个显著的灾害模式是“南涝北旱”。南方,特别是淮河、长江中下游流域,洪涝灾害异常频繁。《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淮、汴、宋、汝、唐、邓、随、郢、复九州大水,漂民庐,坏田稼。” 而北方,尤其是作为帝国统治核心的关中和经济支柱的关东(今河南、山东一带)地区,则饱受干旱之苦。
黄巢起义前的“大旱”前奏:引爆晚唐的黄巢起义,其直接导火索便是关东地区一场持续数年的毁灭性旱灾。《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记载得尤为明确,在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关东仍岁饥,河南尤甚。民且流亡,去乡南渡,过淮、涉江,蔓延数十州。所过剽掠,善为盗者,相与学习,多为群盗。” 次年(875年),旱情与蝗灾并发,“春夏大旱,草木皆枯,饿殍满野。” 这种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状,为王仙芝、黄巢的起义提供了数以十万计的绝望流民。
流传的末世民谣:灾难的深重,甚至催生了预示王朝末日的民谣。据《旧唐书·僖宗纪》记载,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金色虾蟆”暗指身穿黄色战袍的黄巢,而“翻却曹州”则精准地预言了起义的爆发地。这首歌谣的流传,本身就反映了天灾之下民心思变的社会心理。
罕见的寒冬与瘟疫:气候变冷不仅表现为旱涝,还有严酷的寒冬。《旧唐书·五行志》中多次记载了淮河、汉水等南方河流封冻的记录,这在盛唐时期是难以想象的。严寒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的短缺。同时,水灾、旱灾之后,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瘟疫。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旱灾蝗灾之后,《旧唐书》紧接着就记录了大疫的发生,这对挣扎求生的民众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说晚唐的朝廷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那么持续的天灾就是不断拍打它的惊涛骇浪。
摧毁经济基础: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财政收入日益依赖于南方的漕运和盐铁专卖。连年的水旱灾害,严重打击了江淮这一财赋重地,使得朝廷财政濒临崩溃。同时,北方旱灾则摧毁了帝国赖以生存的粮食产区。当朝廷既无钱又无粮时,其对地方的控制力,尤其是对藩镇的约束力,便急剧下降。
瓦解社会结构:唐朝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在安史之乱后已基本瓦解,代之以两税法。两税法以土地和资产为征收对象,在灾年也无法轻易减免。当农民因天灾颗粒无收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弃地而逃,成为流人。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脱离了朝廷的户籍控制,不仅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更是起义军最直接的兵源。王仙芝、黄巢的军队能在短时间内从数千人扩张到数十万人,靠的就是吸纳这些走投无路的饥民。
丧失统治合法性:“天人感应”的观念在唐代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持续而酷烈的自然灾害,被广泛视为上天对李唐皇室失去“天命”的惩罚。朝廷在灾害面前的无能为力——赈灾不力、官员贪腐——更让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当黄巢以“冲天大将军”自居,并打出“天补平均”的口号时,他实际上是在争夺对“天意”的解释权,从而为其推翻唐朝的行动提供合法性。
北宋
气候背景:温暖期中的致命波动
从宏观上看,整个北宋时期(公元960-1127年)大致处于“中世纪温暖期”的范畴内。相对温暖的气候在北宋前期和中期促进了农业发展,尤其是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支撑了其空前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城市文明。
然而,进入12世纪,即宋徽宗在位的政和、重和、宣和年间(公元1111-1125年),全球气候开始出现剧烈波动,表现为气温下降、降水异常,作为“小冰期”到来的前兆。这一时期,气候的稳定性被打破,水、旱、蝗、疫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都显著增加,对这个庞大帝国的农业命脉构成了严峻挑战。
《宋史》中的“五行志”和本纪部分,为我们提供了北宋末年天灾频发的铁证,其记录之密集,灾情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黄河决溢,水患滔天:黄河在北宋本就水患频繁,但在徽宗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宋史·五行志》记载,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河决广济军”。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再次大决口,洪水泛滥于河北、京东等地,“坏田三十万顷”。大水不仅淹没农田,摧毁家园,还直接导致了大规模的饥荒和流民。
江南大水与东南大疫:作为帝国财赋重地的江南地区也未能幸免。据《宋史》记载,崇宁四年(1105年),“浙江大水,杭、越、湖、秀、常、润六州民被灾者五十余万户”。大水过后往往紧随着大疫。大观三年(1109年),“京师大疫”;政和三年(1113年),史载“天下疫”,尤其是两浙、江东、福建等地疫情尤为严重,死者无数。
旱蝗并发,赤地千里:在部分地区遭受水灾的同时,另一些地方则饱受大旱和蝗灾之苦。《宋史·徽宗本纪》载,大观元年(1107年),“京东西、淮南、两浙、江东西、荆湖北路旱”。旱灾往往伴随着蝗灾,政和六年(1116年),“山东、京东、河北、京畿蝗”。水旱蝗疫并发,使得民众辗转于不同灾难之间,几乎没有喘息之机。
罕见天象与地震:除了水、旱、蝗、疫这些“常规”灾害,徽宗朝还充满了各种被视为不祥之兆的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宋史》中关于这一时期“雨木冰”(冻雨)、“冬雷”、“陨石”的记载不绝于书。政和四年(1114年),京师地震。这些灾异在“天人感应”思想的笼罩下,被普遍解读为上天对统治者失德的严重警告。
如果说天灾是上天的警告,那么宋徽宗朝的“人祸”则将这警告的后果放大了无数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
宋徽宗是一位艺术造诣极高的皇帝,但他对奇花异石的病态追求,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为了在京城修建豪华园林“艮岳”,设立“应奉局”,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大肆搜刮奇花异石,并通过运河漕运至京师,这就是“花石纲”。
放大天灾恶果:江南地区本就遭受水灾和瘟疫的侵袭,民力已十分困乏。“花石纲”的差役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运输一块巨石,往往“毁屋拆墙,凿河断桥”,强征数千民夫,耗费无数钱粮。正常的农业生产和救灾漕运被严重挤占和破坏,使得灾民处境愈发艰难。
催生惊天民变:《宋史·方腊传》明确指出,方腊起义的直接原因就是“花石纲”的骚扰。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是“花石纲”的重点搜刮区,当地百姓不堪其苦。方腊正是利用了这种普遍的怨恨,以摩尼教(明教)为组织形式,喊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口号,迅速聚集了数十万追随者,这场起义席卷江南六州五十二县。
南宋
气候背景:小冰期的严酷序幕
南宋的最后几十年,恰逢全球气候由中世纪温暖期向小冰期过渡的关键阶段。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指出,12世纪之后,中国的气候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冷趋势。到了13世纪中后期,这种趋势愈发显著,表现为冬季异常寒冷、生长季节缩短、旱涝灾害频发。南宋的疆域主要集中在亚热带的江南地区,其经济命脉——水稻农业——对气候的稳定性高度依赖。这一轮剧烈的气候突变,无疑是对其国力的致命考验。
查阅《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南宋末代皇帝度宗、恭帝、端宗及帝昰时期(约公元1265-1279年)的灾异记录,其密度和烈度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仿佛整个王朝都被灾难的阴云所笼罩。
水旱交侵,财赋之地沦为泽国饿乡:作为南宋生命线的两浙、江东、福建路,在王朝末期遭受了毁灭性的水旱灾害。《宋史·五行志》记载,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两浙、江东西、福建大水”;而仅仅两年后的咸淳九年(1273年),“春夏大旱,浙西尤甚,米价踊贵”。就在这一年,坚守了六年的襄阳城最终陷落,南宋的门户洞开。连年的水旱灾害不仅导致粮食绝收,更直接摧毁了朝廷最主要的财税来源地,使得前线军费的筹措变得难以为继。
大疫横行,户口凋零:水旱之后,必有大疫。史料中关于南宋末年瘟疫的记载极为惨烈。**咸淳七年(1271年)的大水之后,《宋史》明确记载“民多疫死”。据学者统计,仅台州一地,咸淳八年(1272年)的死亡人数就高达4.7万,而到咸淳十年(1274年),死亡人数更是攀升至惊人的9.7万。遍及东南的瘟疫,使得本就因饥荒而挣扎的民众大量死亡,社会劳动力锐减,兵源枯竭,整个社会陷入死寂。
酷寒雪灾与钱塘江冰封:气候变冷的直接证据是罕见的严寒天气。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冬,元军大举南下之际,南方普遍出现严寒天气。《宋史》记载当年“临安大雪,民多冻死”,甚至连南方的标志性大湖——太湖都出现了大面积封冻。更具象征性和战略意义的是,据《元史·伯颜传》记载,当元军主力抵达临安城下时,钱塘江江面竟然结冰,使得元军得以“结冰为梁”,这在气候温暖时期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不仅是一个气候异常的标志,更在心理上给濒临灭亡的南宋朝廷带来了“天命已尽”的巨大冲击。
面对如此酷烈的自然灾害,本应全力救灾、凝聚人心的南宋朝廷,却因权臣贾似道的弊政而将国家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公田法的致命反噬:为了筹集对抗蒙古的军费,贾似道推行了激进的公田法。该法令的核心是,对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官僚和地主,由政府强行购买其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公田”,租给佃户耕种,租金归国家所有。这项政策的初衷是打击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政。然而,当它在天灾频发的背景下被强力推行时,其效果却是灾难性的。在农业普遍绝收的年份,地主阶层本已损失惨重,此时政府再来强行“购买”其赖以为生的土地,无异于趁火打劫。这激起了占有社会绝大多数财富和资源的士大夫、地主阶层的普遍怨恨与激烈抵抗。他们或隐匿田产,或将劣田卖给国家,使得“公田法”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巨大分裂,使得本应一致对外的南宋,在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内部凝聚力。
经济基础的彻底瓦解:连年的天灾已使农业生产濒临崩溃,而“公田法”则进一步打击了农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南宋长期依赖的纸币会子,因滥发早已信用破产,此时在经济凋敝的背景下更是形同废纸。农业的破产与货币的崩溃,意味着南宋的整个经济体系已经瓦解。当元军南下时,许多州县根本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因为府库里既无粮也无钱。
社会动员能力的丧失:一个健康的社会,在面对外敌时能够动员其民众和资源进行抵抗。然而,南宋末年的社会已病入膏肓。民众在饥荒、瘟疫和酷寒中挣扎求生,朝廷非但无力救济,反而以“公田法”等形式加重其负担。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时,为国尽忠便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元军南下过程中,沿途州县望风而降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并非全是官员将领贪生怕死,更是因为其背后的社会基础已经彻底崩塌,无法再支撑起一场有效的全民战争。
元朝
气候背景:小冰期的全面降临
与唐宋大部分时间所处的中世纪温暖期不同,元朝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气候趋向干冷的阴影之下。到了14世纪中叶,即元朝的最后几十年(元顺帝至正年间),小冰期的特征变得极为显著。这一时期,全球气温普遍下降,导致中国的气候格局发生剧变:北方旱灾愈发频繁酷烈,降水则异常集中,极易引发大洪水,生态系统变得极度脆弱。这种宏观气候背景,对于一个同时需要维持农耕区稳定和草原游牧区安定的庞大帝国来说,是根本性的挑战。
元朝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元史》的“本纪”和“五行志”,堪称一部触目惊心的灾难编年史。天灾的频率、广度和烈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黄河的惊天一变:在所有灾难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黄河的决口与改道。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史·顺帝纪》记载,“河决白茅堤,泛滥十六郡,平地水深二丈。” 洪水淹没了今天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的大片土地,数百万顷良田变为泽国,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这次决口彻底改变了黄河下游的河道,使其不再夺淮入海,而是改由今天山东利津一带入渤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生态浩劫。
无尽的旱灾、蝗灾与大饥:在黄河泛滥的同时,全国其他地区则饱受旱灾和蝗灾之苦。《元史》中“大旱”、“大饥”、“人相食”的记载在至正年间俯拾皆是。例如,至正元年(1341年),“京畿、河南、山东、江浙、湖广大旱”。至正十三年(1353年),京畿地区“大饥,人相食”。旱灾与蝗灾往往如影随形,进一步摧毁了所剩无几的农业收成。
地震频发与大疫流行:地质活动在这一时期也异常活跃。《元史·五行志》记载,至正七年(1347年),仅“京畿、河南、江浙、湖广、福建、四川地震”的记录就多达十余次。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西发生强烈地震,“郡邑城郭、官民庐舍、仓库倒塌者不可胜计”。更致命的是,灾难之后的大规模瘟疫。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水灾后,史载河北、山东等地“民大疫”。有研究认为,肆虐欧洲的“黑死病”与此一时期东亚的鼠疫大爆发有着密切联系,元末的中国正是这场全球性大瘟疫的重灾区之一。
面对如此巨大的天灾,元朝统治者的应对措施非但没有缓解危机,反而成为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
治河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344年黄河决口后,元廷内部对是否治理长期争论不休,导致灾区民众在洪水中浸泡了数年之久。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丞相脱脱才力排众议,决定强行“修复”黄河故道。为此,元廷征发了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的民工达十五万,并派兵监督。这些民工本就是黄泛区的灾民,早已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如今又被强征去从事极其艰苦的治河徭役,官吏的督责与克扣更是家常便饭。绝望的情绪在数十万聚集的民工中迅速蔓延,黄河工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石人一只眼”与红巾军的爆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刘福通等人抓住了时机。他们在即将开挖的河道中预先埋下一个独眼石人,并四处散播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民工们挖出石人时,无不惊为天意,积压已久的愤怒瞬间爆发。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揭竿而起,头裹红巾,史称“红巾军起义”。起义的烈火以治河工地为中心,迅速燃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济崩溃与政治腐败的助燃:除了治河这一直接导火索,元末的社会早已危机四伏。
钞法崩溃:元朝以纸币(交钞、宝钞)为主要货币,但由于政府滥发无度,早已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到元末,纸币几乎形同废纸。天灾来临时,国家既无实物储备进行有效赈济,百姓手中的纸币也无法换来粮食,经济秩序彻底崩溃。
民族矛盾与腐败:元朝的“四等人制”造成了深刻的民族隔阂与不公。蒙古和色目贵族享有特权,对汉人、南人的压迫和剥削极其严重。朝廷内部权斗不断,各级官吏贪腐成风,使得任何救灾措施都无法落到实处。
明朝
气候背景:小冰期的致命一击
整个明朝(公元1368-1644年)都处于全球性的“小冰期”中,但其最寒冷、最不稳定的时期,恰好出现在明朝的最后七十余年,即从万历后期至崇祯末年。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晚明小冰期”或“蒙德极小期”,太阳活动异常减弱,导致地球接收的辐射量减少,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剧变。
具体表现为:
气温显著下降:年平均气温比现今低约1-2℃,冬季尤为酷寒,南方地区频繁出现大规模降雪和江河封冻的记录。
旱涝格局巨变:夏季风(东亚季风)急剧衰退,导致传统上湿润的南方变得干旱,而本就干旱的北方则因水汽无法抵达而陷入了持续数十年的特大旱灾。
晚明的史料,无论是官方的《明实录》、《明史》,还是地方志和私人笔记,都充满了关于灾异的血泪记载,其密度、广度和烈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极值点。
持续的大旱——王朝的绞索:旱灾,是勒在明王朝脖子上最致命的绞索。从万历末年开始,以陕西、山西、河南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就陷入了持续的、毁灭性的干旱之中。《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大旱,赤地千里。” 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此后的十几年里,旱灾范围不断扩大,强度不断升级。崇祯十三年(1640年),灾情达到顶峰,“南北俱大旱……河南及山、陕、江、浙、湖、广,皆赤地千里,民大饥,人相食。” 连年的干旱使得土地龟裂,禾苗枯死,农业生产被彻底摧毁。
蝗灾伴生,如影随形:大旱之后,必有大蝗。干旱的环境为蝗虫的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史载崇祯年间的蝗灾“飞蝗蔽天”、“食苗稼尽”、“所过寸草不留”。例如,崇祯十年(1637年),京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同时爆发大蝗灾。民众在饥饿之余,还要面对这“飞来的饥荒”,生存希望被彻底剥夺。
大疫横行——最后的审判:当民众在饥饿中挣扎,被迫啃食树皮、草根,甚至“观音土”,乃至易子而食时,他们的抵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为瘟疫的爆发提供了温床。晚明末年,一场被称为“疙瘩病”或“大头瘟”(据考证可能为鼠疫)的特大瘟疫在中国北方肆虐。崇祯十六年(1643年),疫情在北京城内大爆发,“京师大疫,死者无算”,甚至有“十室九空”的惨状。据估计,北京城内因瘟疫死亡的人口可能达到数十万。这场瘟疫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更使得北京的守城兵力锐减,战斗力几乎崩溃。当李自成的军队兵临城下时,他们面对的是一座被瘟疫掏空了的死亡之城。
南方的酷寒与“天人感应”:在北方被旱、蝗、疫反复蹂躏的同时,通常温暖的南方也出现了罕见的极端低温天气。《江南通志》记载,明末江苏、浙**地频繁出现夏季降雪、太湖封冻数尺的异象。崇祯十四年(1641年),连处在亚热带的广东都出现了“陨雪”的记录。在“天人感应”的传统观念下,这种“夏雪冬雷”的反常天象,被普遍视为王朝气数已尽的终极凶兆,极大地动摇了人心。
参考文献
竺可桢. (1972).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考古学报, (1), 15-38.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相关研究成果(综合自新闻报道及学术论文)。
《史记》,司马迁,汉代。
《汉书》,班固,汉代。
里耶秦简相关考古报告及研究论文。
张兰生 主编. (1993). 中国生存环境演变规律研究. 海洋出版社.
侯仁之 主编. (1996). 环境变迁研究. 辽宁古籍出版社.
陈彦良. 两汉灾害高峰期——天灾、人祸与治乱盛衰的关联性分析. 新史学, 27(1), 47-111.
蒲坚. (2007). 东汉晚期的疾疫与宗教.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78(2), 245-296.
王子今. (2012).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历史研究, (1), 49-61.
《旧唐书》,刘昫等,后晋.
《新唐书》,欧阳修、宋祁等,北宋.
《资治通鉴》,司马光,北宋.
满志敏. (2009). 气候变化与唐代社会盛衰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3), 5-18.
张家诚. (1987). 唐代气候的冷暖变迁. 历史地理, (5), 1-13.
蓝勇. (2002). 历史时期西南环境与社会研究. 人民出版社.
《宋史》,脱脱等,元.
《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南宋.
《鸡肋编》,庄绰,宋.
伊懋可 (Mark Elvin). (2008).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发展模式. (中译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邓云特. (1962). 中国救荒史. 商务印书馆.
《元史》,宋濂等,明.
吴钩. (2018). 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中涉及对南宋末年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
方志远. (2010). <宋史>札记. 江西高校出版社.
韩茂莉. (2012). 14世纪气候变动与元末农民战争.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陈高佣. (1982). 元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中华书局.
萧启庆. (2007). 蒙元史新研. 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Timothy Brook.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明史》,张廷玉等,清.
《明实录》,明代官修编年史.
《崇祯长编》,汪楫,清.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其中有关于小冰期对元明影响的详细论述).
满志敏. (2015). 明末大旱与明王朝的覆亡.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萧凌. (2007). 晚明华北地区鼠疫猖獗考. 北京社会科学.
Parker, Geoffrey. (2013).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