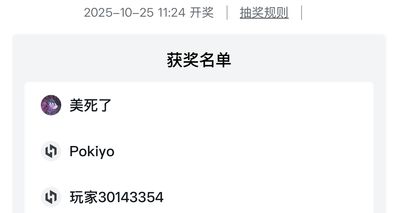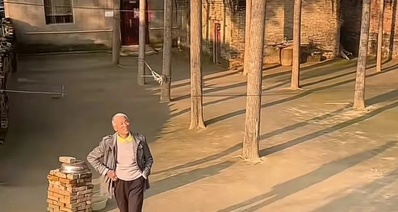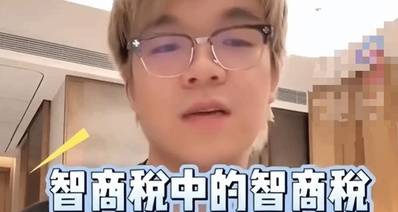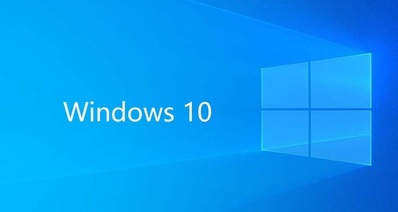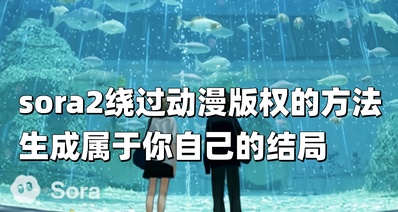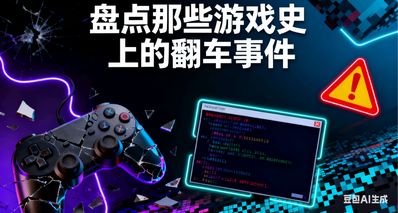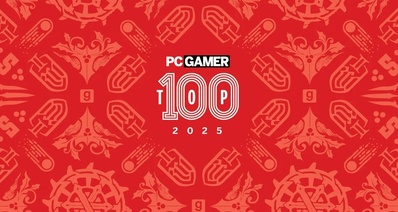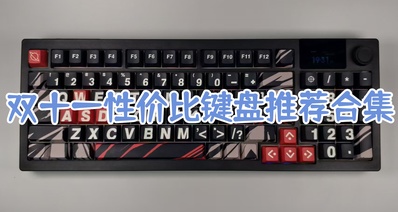秦朝
氣候背景:從溫暖期到乾冷期的轉折
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秦朝的建立(公元前221年)處於一個相對溫暖溼潤的氣候時期,這爲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秦統一六國的戰爭消耗。然而,秦朝末年至漢朝初年,中國氣候經歷了一個由暖溼向乾冷的轉折期。這種氣候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但其帶來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尤其是對於一個以農業爲立國之本的龐大帝國。
儘管秦朝歷史短暫,留下的史料有限,但我們仍能從一些文獻中窺見其末年天災的蹤跡。
《史記·秦始皇本紀》 雖未直接詳盡記載秦末的全國性大旱,但在描述陳勝吳廣起義的背景時提到,“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這場“大雨”雖是局部事件,卻直接點燃了反秦的導火索。值得注意的是,極端降雨事件也常常是氣候異常的表現之一。
雖然直接記載秦末災害的文獻不多,但我們可以從漢初的記錄中反推秦末的情況。《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漢初“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 賈誼在《論積貯疏》中也描繪了漢初“人相食”的慘狀。這種大規模的饑荒,除了戰爭破壞外,往往與之前的農業歉收緊密相關,而農業歉收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旱災、洪澇等自然災害。
有研究指出,秦漢時期關中地區的環境承載力開始下降。戰國時期,蘇秦形容關中爲“天府”,“田肥美,民殷富”。 但到了東漢,班固在《兩都賦》中只能說關中“號爲近蜀”,其富庶程度已不及成都平原。這種變化的背後,除了政治中心的轉移,也與氣候趨於乾旱、水資源減少等環境因素有關。
2002年在湖南里耶出土的大量秦代簡牘,爲我們瞭解秦朝的基層社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詳實資料。 裏耶秦簡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戶籍、田租、賦稅、徭役、司法、郵傳等方方面面。
簡牘中詳細記錄了軍隊和官吏的糧食消耗量,以及對土地開墾和農業生產的嚴格管理。這種精細到極致的管理,一方面體現了秦朝強大的國家機器,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其物資儲備可能並不寬裕,應對大規模自然災害的能力相對脆弱。一旦氣候變化導致糧食大面積減產,這種高度緊張的社會結構就容易崩潰。
東漢
氣候背景:由暖轉寒的開端
科學研究表明,從西漢末年開始,中國氣候經歷了一次明顯的轉折,由相對溫暖溼潤期轉向乾冷期。這一轉變深刻影響了以農業爲本的漢帝國。竺可楨先生在其不朽著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便指出,西漢大部分時間處於一個溫暖期,但自西漢末年起,氣候開始波動並趨於寒冷。這一宏觀背景,使得漢代末年的農業生產變得極爲脆弱。
西漢的末代皇帝,尤其是漢成帝、漢哀帝時期,史書中的災異記載陡然增多,形成了一條清晰的災難鏈條,預示着王朝的危機。
水旱頻仍與糧食危機:《漢書·五行志》中充滿了西漢末年災害的記錄。例如,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郡國三十餘飢,民流離, 就谷關東。” 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關東大水,飢,民相食。” 持續的水旱災害直接摧毀了農業生產,導致大規模的饑荒和流民潮。
罕見的霜雪與風災:氣候變冷的直接證據便是反常的霜雪天氣。《漢書·王莽傳》記載,天鳳元年(公元14年),“四月,隕霜,殺屮木,海瀕尤甚。”初夏降霜,對農作物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此外,沙塵暴等風災也異常頻繁,《漢書·五行志》描述漢成帝時的一次強沙塵暴:“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着地者黃土塵也。”
地震頻發:《漢書》同樣記載了多次強烈地震。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 地震不僅造成直接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更在“天人感應”的時代背景下,嚴重動搖了人們對皇權穩固的信心。
災異、讖緯與王莽篡漢
在漢代,董仲舒建立的“天人感應”學說深入人心,災異被普遍認爲是上天對統治者失德的警告。西漢末年接連不斷的災難,使得“漢運已衰”的觀念瀰漫於社會上下。王莽正是利用了這種社會心理,將自己塑造爲順天應命的“聖人”。
他一方面以儒生的姿態出現,積極救災,收買人心。據記載,西漢末年饑荒和瘟疫導致“死者以百萬數”,而朝廷應對無力。王莽則以大司馬的身份建立醫療點,甚至自掏腰包安葬死者,極大地博取了民衆的好感。另一方面,他與儒生們大肆宣揚符命讖記,將每一次自然災害都解讀爲漢室氣數已盡、需要“改朝換代”的證據。最終,在天災不斷、人心思變的背景下,王莽以和平禪讓的方式,終結了西漢的統治,建立了新朝。可以說,西漢的滅亡,天災是爲其敲響的喪鐘,而王莽則是在鐘聲裏登臺的野心家。
如果說西漢的滅亡是慢性病,那麼東漢的傾覆則更像是一場急性重症,而其病竈同樣深植於天災的溫牀。
西漢
氣候背景:小冰期的嚴酷考驗
現代學者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東漢末年恰逢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小冰期”,氣候異常寒冷,自然災害的頻率和強度都遠超前代。這一時期的災害記錄,在《後漢書·五行志》中更是觸目驚心。
瘟疫——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所有天災中,對東漢末年社會衝擊最大的莫過於連年不斷的大規模瘟疫。桓、靈二帝時期(公元147-189年)是疾疫的集中爆發期。
史不絕書的疫情:《後漢書·孝桓帝紀》和《孝靈帝紀》明確記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京師疾疫”,同年“九江、廬江大疫”;延熹四年(161年),“春正月,大疫”;靈帝建寧四年(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年),“春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到黃巾起義後的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短短三十餘年間,有明確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就多達七八次,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見。曹植的詩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正是當時社會凋敝的真實寫照。
與天災的惡性循環:瘟疫的爆發往往與水旱、蝗災等其他災害相伴相生。例如,熹平六年(177年),“夏四月,大旱”,同年“七州蝗”。大旱導致饑荒,民衆易子而食,抵抗力下降,流離失所又加速了疫病的傳播。此外,地震、洪水、冰雹等災害也頻繁發生。如靈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極度的嚴寒進一步加劇了民間的苦難。
面對連綿不絕的天災和腐朽不堪、無所作爲的朝廷,數以千萬計的民衆陷入了絕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角創立的太平道應運而生。
《太平經》作爲其核心經典,本身就包含了對現實災難的解釋和對理想“太平”世界的嚮往。張角以“大賢良師”自居,核心手段便是“符水治病”。在瘟疫橫行、求醫無門的亂世,張角的太平道爲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姓提供了精神慰藉和最基本的醫療救助,因此迅速發展,“十餘年間,衆數十萬,遍於八州”。
當政治黑暗與天災人禍達到頂點時,張角振臂一呼,喊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數十萬頭裹黃巾的饑民與信徒揭竿而起,雖然起義最終被鎮壓,但它卻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並直接導致了地方州牧擁兵自重、軍閥割據的局面,漢朝的喪鐘就此被徹底敲響。
唐朝
現代氣候學研究普遍認爲,唐朝的前半期,尤其是盛唐開元、天寶年間,正處於中國歷史上一個相對溫暖溼潤的時期,被稱爲“隋唐溫暖期”。溫暖的氣候爲農業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關中地區物產豐饒,支持了長安城的繁榮和帝國的對外擴張。杜甫詩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描繪,既是開元盛世的寫照,也離不開良好氣候的支撐。
晚唐的“小冰期”前奏
然而,以安史之亂(公元755年)爲分水嶺,唐朝的氣候開始發生顯著轉變,逐步進入一個持續乾冷、旱澇災害交替頻發的時期。這一氣候轉型期,被一些學者視爲全球“中世紀溫暖期”的結束和“小冰期”的開端。持續的低溫和不穩定的降水,使得農業生產的風險急劇增高,尤其是在北方地區。
晚唐的史籍,特別是《舊唐書》與《新唐書》的“五行志”以及《資治通鑑》,詳細記錄了這一時期觸目驚心的天災。
南澇北旱的格局形成:安史之亂後,一個顯著的災害模式是“南澇北旱”。南方,特別是淮河、長江中下游流域,洪澇災害異常頻繁。《新唐書·五行志》記載,唐代宗大曆四年(公元769年),“淮、汴、宋、汝、唐、鄧、隨、郢、復九州大水,漂民廬,壞田稼。” 而北方,尤其是作爲帝國統治核心的關中和經濟支柱的關東(今河南、山東一帶)地區,則飽受乾旱之苦。
黃巢起義前的“大旱”前奏:引爆晚唐的黃巢起義,其直接導火索便是關東地區一場持續數年的毀滅性旱災。《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二》記載得尤爲明確,在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關東仍歲飢,河南尤甚。民且流亡,去鄉南渡,過淮、涉江,蔓延數十州。所過剽掠,善爲盜者,相與學習,多爲羣盜。” 次年(875年),旱情與蝗災併發,“春夏大旱,草木皆枯,餓殍滿野。” 這種赤地千里、餓殍遍地的慘狀,爲王仙芝、黃巢的起義提供了數以十萬計的絕望流民。
流傳的末世民謠:災難的深重,甚至催生了預示王朝末日的民謠。據《舊唐書·僖宗紀》記載,當時民間流傳着這樣的歌謠:“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 “金色蝦蟆”暗指身穿黃色戰袍的黃巢,而“翻卻曹州”則精準地預言了起義的爆發地。這首歌謠的流傳,本身就反映了天災之下民心思變的社會心理。
罕見的寒冬與瘟疫:氣候變冷不僅表現爲旱澇,還有嚴酷的寒冬。《舊唐書·五行志》中多次記載了淮河、漢水等南方河流封凍的記錄,這在盛唐時期是難以想象的。嚴寒進一步加劇了糧食的短缺。同時,水災、旱災之後,往往伴隨着大規模的瘟疫。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旱災蝗災之後,《舊唐書》緊接着就記錄了大疫的發生,這對掙扎求生的民衆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說晚唐的朝廷是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那麼持續的天災就是不斷拍打它的驚濤駭浪。
摧毀經濟基礎:安史之亂後,唐朝的財政收入日益依賴於南方的漕運和鹽鐵專賣。連年的水旱災害,嚴重打擊了江淮這一財賦重地,使得朝廷財政瀕臨崩潰。同時,北方旱災則摧毀了帝國賴以生存的糧食產區。當朝廷既無錢又無糧時,其對地方的控制力,尤其是對藩鎮的約束力,便急劇下降。
瓦解社會結構:唐朝以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爲基礎的社會管理體系在安史之亂後已基本瓦解,代之以兩稅法。兩稅法以土地和資產爲徵收對象,在災年也無法輕易減免。當農民因天災顆粒無收時,唯一的選擇就是棄地而逃,成爲流人。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流民,脫離了朝廷的戶籍控制,不僅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更是起義軍最直接的兵源。王仙芝、黃巢的軍隊能在短時間內從數千人擴張到數十萬人,靠的就是吸納這些走投無路的饑民。
喪失統治合法性:“天人感應”的觀念在唐代依然有巨大的影響力。持續而酷烈的自然災害,被廣泛視爲上天對李唐皇室失去“天命”的懲罰。朝廷在災害面前的無能爲力——賑災不力、官員貪腐——更讓這種觀念深入人心。當黃巢以“沖天大將軍”自居,並打出“天補平均”的口號時,他實際上是在爭奪對“天意”的解釋權,從而爲其推翻唐朝的行動提供合法性。
北宋
氣候背景:溫暖期中的致命波動
從宏觀上看,整個北宋時期(公元960-1127年)大致處於“中世紀溫暖期”的範疇內。相對溫暖的氣候在北宋前期和中期促進了農業發展,尤其是占城稻的引進與推廣,支撐了其空前繁榮的商品經濟和城市文明。
然而,進入12世紀,即宋徽宗在位的政和、重和、宣和年間(公元1111-1125年),全球氣候開始出現劇烈波動,表現爲氣溫下降、降水異常,作爲“小冰期”到來的前兆。這一時期,氣候的穩定性被打破,水、旱、蝗、疫等災害的發生頻率和強度都顯著增加,對這個龐大帝國的農業命脈構成了嚴峻挑戰。
《宋史》中的“五行志”和本紀部分,爲我們提供了北宋末年天災頻發的鐵證,其記錄之密集,災情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
黃河決溢,水患滔天:黃河在北宋本就水患頻繁,但在徽宗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宋史·五行志》記載,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河決廣濟軍”。政和七年(1117年),黃河再次大決口,洪水氾濫於河北、京東等地,“壞田三十萬頃”。大水不僅淹沒農田,摧毀家園,還直接導致了大規模的饑荒和流民。
江南大水與東南大疫:作爲帝國財賦重地的江南地區也未能倖免。據《宋史》記載,崇寧四年(1105年),“浙江大水,杭、越、湖、秀、常、潤六州民被災者五十餘萬戶”。大水過後往往緊隨着大疫。大觀三年(1109年),“京師大疫”;政和三年(1113年),史載“天下疫”,尤其是兩浙、江東、福建等地疫情尤爲嚴重,死者無數。
旱蝗併發,赤地千里:在部分地區遭受水災的同時,另一些地方則飽受大旱和蝗災之苦。《宋史·徽宗本紀》載,大觀元年(1107年),“京東西、淮南、兩浙、江東西、荊湖北路旱”。旱災往往伴隨着蝗災,政和六年(1116年),“山東、京東、河北、京畿蝗”。水旱蝗疫併發,使得民衆輾轉於不同災難之間,幾乎沒有喘息之機。
罕見天象與地震:除了水、旱、蝗、疫這些“常規”災害,徽宗朝還充滿了各種被視爲不祥之兆的極端天氣和地質災害。《宋史》中關於這一時期“雨木冰”(凍雨)、“冬雷”、“隕石”的記載不絕於書。政和四年(1114年),京師地震。這些災異在“天人感應”思想的籠罩下,被普遍解讀爲上天對統治者失德的嚴重警告。
如果說天災是上天的警告,那麼宋徽宗朝的“人禍”則將這警告的後果放大了無數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綱。
宋徽宗是一位藝術造詣極高的皇帝,但他對奇花異石的病態追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爲了在京城修建豪華園林“艮嶽”,設立“應奉局”,在以蘇州爲中心的江南地區大肆搜刮奇花異石,並通過運河漕運至京師,這就是“花石綱”。
放大天災惡果:江南地區本就遭受水災和瘟疫的侵襲,民力已十分睏乏。“花石綱”的差役更是雪上加霜。爲了運輸一塊巨石,往往“毀屋拆牆,鑿河斷橋”,強徵數千民夫,耗費無數錢糧。正常的農業生產和救災漕運被嚴重擠佔和破壞,使得災民處境愈發艱難。
催生驚天民變:《宋史·方臘傳》明確指出,方臘起義的直接原因就是“花石綱”的騷擾。睦州青溪縣(今浙江淳安)是“花石綱”的重點搜刮區,當地百姓不堪其苦。方臘正是利用了這種普遍的怨恨,以摩尼教(明教)爲組織形式,喊出了“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口號,迅速聚集了數十萬追隨者,這場起義席捲江南六州五十二縣。
南宋
氣候背景:小冰期的嚴酷序幕
南宋的最後幾十年,恰逢全球氣候由中世紀溫暖期向小冰期過渡的關鍵階段。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指出,12世紀之後,中國的氣候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冷趨勢。到了13世紀中後期,這種趨勢愈發顯著,表現爲冬季異常寒冷、生長季節縮短、旱澇災害頻發。南宋的疆域主要集中在亞熱帶的江南地區,其經濟命脈——水稻農業——對氣候的穩定性高度依賴。這一輪劇烈的氣候突變,無疑是對其國力的致命考驗。
查閱《宋史》和《續資治通鑑》,南宋末代皇帝度宗、恭帝、端宗及帝昰時期(約公元1265-1279年)的災異記錄,其密度和烈度都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彷彿整個王朝都被災難的陰雲所籠罩。
水旱交侵,財賦之地淪爲澤國餓鄉:作爲南宋生命線的兩浙、江東、福建路,在王朝末期遭受了毀滅性的水旱災害。《宋史·五行志》記載,宋度宗鹹淳七年(公元1271年),“兩浙、江東西、福建大水”;而僅僅兩年後的鹹淳九年(1273年),“春夏大旱,浙西尤甚,米價踊貴”。就在這一年,堅守了六年的襄陽城最終陷落,南宋的門戶洞開。連年的水旱災害不僅導致糧食絕收,更直接摧毀了朝廷最主要的財稅來源地,使得前線軍費的籌措變得難以爲繼。
大疫橫行,戶口凋零:水旱之後,必有大疫。史料中關於南宋末年瘟疫的記載極爲慘烈。**鹹淳七年(1271年)的大水之後,《宋史》明確記載“民多疫死”。據學者統計,僅台州一地,鹹淳八年(1272年)的死亡人數就高達4.7萬,而到鹹淳十年(1274年),死亡人數更是攀升至驚人的9.7萬。遍及東南的瘟疫,使得本就因饑荒而掙扎的民衆大量死亡,社會勞動力銳減,兵源枯竭,整個社會陷入死寂。
酷寒雪災與錢塘江冰封:氣候變冷的直接證據是罕見的嚴寒天氣。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冬,元軍大舉南下之際,南方普遍出現嚴寒天氣。《宋史》記載當年“臨安大雪,民多凍死”,甚至連南方的標誌性大湖——太湖都出現了大面積封凍。更具象徵性和戰略意義的是,據《元史·伯顏傳》記載,當元軍主力抵達臨安城下時,錢塘江江面竟然結冰,使得元軍得以“結冰爲梁”,這在氣候溫暖時期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這不僅是一個氣候異常的標誌,更在心理上給瀕臨滅亡的南宋朝廷帶來了“天命已盡”的巨大沖擊。
面對如此酷烈的自然災害,本應全力救災、凝聚人心的南宋朝廷,卻因權臣賈似道的弊政而將國家推向了更深的深淵。
公田法的致命反噬:爲了籌集對抗蒙古的軍費,賈似道推行了激進的公田法。該法令的核心是,對擁有百畝以上土地的官僚和地主,由政府強行購買其三分之一的土地作爲“公田”,租給佃戶耕種,租金歸國家所有。這項政策的初衷是打擊土地兼併、增加國家財政。然而,當它在天災頻發的背景下被強力推行時,其效果卻是災難性的。在農業普遍絕收的年份,地主階層本已損失慘重,此時政府再來強行“購買”其賴以爲生的土地,無異於趁火打劫。這激起了佔有社會絕大多數財富和資源的士大夫、地主階層的普遍怨恨與激烈抵抗。他們或隱匿田產,或將劣田賣給國家,使得“公田法”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更嚴重的是,它造成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巨大分裂,使得本應一致對外的南宋,在最關鍵的時刻失去了內部凝聚力。
經濟基礎的徹底瓦解:連年的天災已使農業生產瀕臨崩潰,而“公田法”則進一步打擊了農業投資的積極性。同時,南宋長期依賴的紙幣會子,因濫發早已信用破產,此時在經濟凋敝的背景下更是形同廢紙。農業的破產與貨幣的崩潰,意味着南宋的整個經濟體系已經瓦解。當元軍南下時,許多州縣根本無力組織有效的抵抗,因爲府庫裏既無糧也無錢。
社會動員能力的喪失:一個健康的社會,在面對外敵時能夠動員其民衆和資源進行抵抗。然而,南宋末年的社會已病入膏肓。民衆在饑荒、瘟疫和酷寒中掙扎求生,朝廷非但無力救濟,反而以“公田法”等形式加重其負擔。當生存都成爲問題時,爲國盡忠便成了一句空話。因此,元軍南下過程中,沿途州縣望風而降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並非全是官員將領貪生怕死,更是因爲其背後的社會基礎已經徹底崩塌,無法再支撐起一場有效的全民戰爭。
元朝
氣候背景:小冰期的全面降臨
與唐宋大部分時間所處的中世紀溫暖期不同,元朝自始至終都籠罩在氣候趨向乾冷的陰影之下。到了14世紀中葉,即元朝的最後幾十年(元順帝至正年間),小冰期的特徵變得極爲顯著。這一時期,全球氣溫普遍下降,導致中國的氣候格局發生劇變:北方旱災愈發頻繁酷烈,降水則異常集中,極易引發大洪水,生態系統變得極度脆弱。這種宏觀氣候背景,對於一個同時需要維持農耕區穩定和草原遊牧區安定的龐大帝國來說,是根本性的挑戰。
元朝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元史》的“本紀”和“五行志”,堪稱一部觸目驚心的災難編年史。天災的頻率、廣度和烈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黃河的驚天一變:在所有災難中,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是黃河的決口與改道。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元史·順帝紀》記載,“河決白茅堤,氾濫十六郡,平地水深二丈。” 洪水淹沒了今天的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北部的大片土地,數百萬頃良田變爲澤國,數百萬民衆流離失所。這次決口徹底改變了黃河下游的河道,使其不再奪淮入海,而是改由今天山東利津一帶入渤海。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生態浩劫。
無盡的旱災、蝗災與大飢:在黃河氾濫的同時,全國其他地區則飽受旱災和蝗災之苦。《元史》中“大旱”、“大飢”、“人相食”的記載在至正年間俯拾皆是。例如,至正元年(1341年),“京畿、河南、山東、江浙、湖廣大旱”。至正十三年(1353年),京畿地區“大飢,人相食”。旱災與蝗災往往如影隨形,進一步摧毀了所剩無幾的農業收成。
地震頻發與大疫流行:地質活動在這一時期也異常活躍。《元史·五行志》記載,至正七年(1347年),僅“京畿、河南、江浙、湖廣、福建、四川地震”的記錄就多達十餘次。至正十九年(1359年),山西發生強烈地震,“郡邑城郭、官民廬舍、倉庫倒塌者不可勝計”。更致命的是,災難之後的大規模瘟疫。至正四年(1344年)**黃河水災後,史載河北、山東等地“民大疫”。有研究認爲,肆虐歐洲的“黑死病”與此一時期東亞的鼠疫大爆發有着密切聯繫,元末的中國正是這場全球性大瘟疫的重災區之一。
面對如此巨大的天災,元朝統治者的應對措施非但沒有緩解危機,反而成爲了引爆危機的導火索。
治河成爲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1344年黃河決口後,元廷內部對是否治理長期爭論不休,導致災區民衆在洪水中浸泡了數年之久。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丞相脫脫才力排衆議,決定強行“修復”黃河故道。爲此,元廷徵發了汴梁、大名等十三路的民工達十五萬,並派兵監督。這些民工本就是黃泛區的災民,早已飢寒交迫、怨聲載道。如今又被強徵去從事極其艱苦的治河徭役,官吏的督責與剋扣更是家常便飯。絕望的情緒在數十萬聚集的民工中迅速蔓延,黃河工地成了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石人一隻眼”與紅巾軍的爆發: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白蓮教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人抓住了時機。他們在即將開挖的河道中預先埋下一個獨眼石人,並四處散播民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當民工們挖出石人時,無不驚爲天意,積壓已久的憤怒瞬間爆發。至正十一年五月,劉福通在潁州(今安徽阜陽)揭竿而起,頭裹紅巾,史稱“紅巾軍起義”。起義的烈火以治河工地爲中心,迅速燃遍了黃河中下游地區。
經濟崩潰與政治腐敗的助燃:除了治河這一直接導火索,元末的社會早已危機四伏。
鈔法崩潰:元朝以紙幣(交鈔、寶鈔)爲主要貨幣,但由於政府濫發無度,早已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到元末,紙幣幾乎形同廢紙。天災來臨時,國家既無實物儲備進行有效賑濟,百姓手中的紙幣也無法換來糧食,經濟秩序徹底崩潰。
民族矛盾與腐敗:元朝的“四等人制”造成了深刻的民族隔閡與不公。蒙古和色目貴族享有特權,對漢人、南人的壓迫和剝削極其嚴重。朝廷內部權鬥不斷,各級官吏貪腐成風,使得任何救災措施都無法落到實處。
明朝
氣候背景:小冰期的致命一擊
整個明朝(公元1368-1644年)都處於全球性的“小冰期”中,但其最寒冷、最不穩定的時期,恰好出現在明朝的最後七十餘年,即從萬曆後期至崇禎末年。這一時期,又被稱爲“晚明小冰期”或“蒙德極小期”,太陽活動異常減弱,導致地球接收的輻射量減少,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氣候劇變。
具體表現爲:
氣溫顯著下降:年平均氣溫比現今低約1-2℃,冬季尤爲酷寒,南方地區頻繁出現大規模降雪和江河封凍的記錄。
旱澇格局鉅變:夏季風(東亞季風)急劇衰退,導致傳統上溼潤的南方變得乾旱,而本就乾旱的北方則因水汽無法抵達而陷入了持續數十年的特大旱災。
晚明的史料,無論是官方的《明實錄》、《明史》,還是地方誌和私人筆記,都充滿了關於災異的血淚記載,其密度、廣度和烈度,都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極值點。
持續的大旱——王朝的絞索:旱災,是勒在明王朝脖子上最致命的絞索。從萬曆末年開始,以陝西、山西、河南爲中心的中國北方就陷入了持續的、毀滅性的乾旱之中。《明史·五行志》記載,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陝西大旱,赤地千里。” 這僅僅是一個開端。此後的十幾年裏,旱災範圍不斷擴大,強度不斷升級。崇禎十三年(1640年),災情達到頂峯,“南北俱大旱……河南及山、陝、江、浙、湖、廣,皆赤地千里,民大飢,人相食。” 連年的乾旱使得土地龜裂,禾苗枯死,農業生產被徹底摧毀。
蝗災伴生,如影隨形:大旱之後,必有大蝗。乾旱的環境爲蝗蟲的繁殖提供了絕佳條件。史載崇禎年間的蝗災“飛蝗蔽天”、“食苗稼盡”、“所過寸草不留”。例如,崇禎十年(1637年),京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同時爆發大蝗災。民衆在飢餓之餘,還要面對這“飛來的饑荒”,生存希望被徹底剝奪。
大疫橫行——最後的審判:當民衆在飢餓中掙扎,被迫啃食樹皮、草根,甚至“觀音土”,乃至易子而食時,他們的抵抗力降到了最低點,這爲瘟疫的爆發提供了溫牀。晚明末年,一場被稱爲“疙瘩病”或“大頭瘟”(據考證可能爲鼠疫)的特大瘟疫在中國北方肆虐。崇禎十六年(1643年),疫情在北京城內大爆發,“京師大疫,死者無算”,甚至有“十室九空”的慘狀。據估計,北京城內因瘟疫死亡的人口可能達到數十萬。這場瘟疫不僅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更使得北京的守城兵力銳減,戰鬥力幾乎崩潰。當李自成的軍隊兵臨城下時,他們面對的是一座被瘟疫掏空了的死亡之城。
南方的酷寒與“天人感應”:在北方被旱、蝗、疫反覆蹂躪的同時,通常溫暖的南方也出現了罕見的極端低溫天氣。《江南通志》記載,明末江蘇、浙**地頻繁出現夏季降雪、太湖封凍數尺的異象。崇禎十四年(1641年),連處在亞熱帶的廣東都出現了“隕雪”的記錄。在“天人感應”的傳統觀念下,這種“夏雪冬雷”的反常天象,被普遍視爲王朝氣數已盡的終極凶兆,極大地動搖了人心。
參考文獻
竺可楨. (1972).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考古學報, (1), 15-38.
中科院地球環境研究所相關研究成果(綜合自新聞報道及學術論文)。
《史記》,司馬遷,漢代。
《漢書》,班固,漢代。
裏耶秦簡相關考古報告及研究論文。
張蘭生 主編. (1993). 中國生存環境演變規律研究. 海洋出版社.
侯仁之 主編. (1996). 環境變遷研究. 遼寧古籍出版社.
陳彥良. 兩漢災害高峯期——天災、人禍與治亂盛衰的關聯性分析. 新史學, 27(1), 47-111.
蒲堅. (2007). 東漢晚期的疾疫與宗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78(2), 245-296.
王子今. (2012). 兩漢之際氣候變遷與絲綢之路長安—洛陽路段的繁榮. 歷史研究, (1), 49-61.
《舊唐書》,劉昫等,後晉.
《新唐書》,歐陽修、宋祁等,北宋.
《資治通鑑》,司馬光,北宋.
滿志敏. (2009). 氣候變化與唐代社會盛衰研究.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3), 5-18.
張家誠. (1987). 唐代氣候的冷暖變遷. 歷史地理, (5), 1-13.
藍勇. (2002). 歷史時期西南環境與社會研究. 人民出版社.
《宋史》,脫脫等,元.
《續資治通鑑長編》,李燾,南宋.
《雞肋編》,莊綽,宋.
伊懋可 (Mark Elvin). (2008). 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發展模式. (中譯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鄧雲特. (1962). 中國救荒史. 商務印書館.
《元史》,宋濂等,明.
吳鉤. (2018).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書中涉及對南宋末年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
方誌遠. (2010). <宋史>札記. 江西高校出版社.
韓茂莉. (2012). 14世紀氣候變動與元末農民戰爭.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陳高傭. (1982). 元末農民戰爭史料彙編. 中華書局.
蕭啓慶. (2007). 蒙元史新研.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Timothy Brook.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明史》,張廷玉等,清.
《明實錄》,明代官修編年史.
《崇禎長編》,汪楫,清.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2010).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其中有關於小冰期對元明影響的詳細論述).
滿志敏. (2015). 明末大旱與明王朝的覆亡.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蕭凌. (2007). 晚明華北地區鼠疫猖獗考. 北京社會科學.
Parker, Geoffrey. (2013). 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