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第四部第五节审讯片段时突然感到莫名熟悉,特此围绕前面的心理刻画写些随笔,权作娱乐参考。
罗佳走进警察局想要自首,他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监视
“拉斯科利尼科夫是谁,是何许人?他用不安的、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巡视着,想看看:他身边有没有什么押送犯人的卫兵,有没有什么神秘的目光在监视他,不让他逃跑?但是无可疑之处:他只看见那武办事员果猥琐琐、满腹心事的脸,后来他又看到一些人,但是谁也不管他:源怕他马上就走,爱上哪上哪,也没人管他。”
他畏惧所有人的目光,同时暗暗期盼着所有人的目光。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他又似“所有人”。
他有着房东时刻想窥探的心理;他有母亲的仁慈,小心翼翼而深切的爱;他有妹妹的大义与机敏;他有朋友拉组米欣强烈的表达欲与一视同仁的热血;他有医生的高度冷静与漠然;他有女仆与人交往间能既保持距离又紧密相联的联系;他有那位怀疑他的警察的大智若愚与高度机警;他有索菲娅不知所措但要行动的责任感,但最后只能寻求救赎(第五部第四节的描写极为精彩);
而他明明拥有像索菲娅父亲那样的救赎机会:天降三千卢布巨款,足以让家里摆脱贫穷的困境;妹妹杜尼娅得以摆脱虚伪的未婚夫,重获自由;好友拉组米欣也正雄心勃勃地邀请大家一同创业,生活眼看欣欣向荣——然而,他却骤然决定断绝一切关系,兀自离去。
他在第一次见面时便洞穿卢仁潜在的阴暗想法,正因他完全理解这种“地下室人”般的孤傲,所以极力反对其与妹妹的亲事;(当然,看到后面说这玩意“地下室人”都算抬举他了)
他在某种程度与斯维德里盖洛夫极为相似,后者实质上是他理论的终点,他所有的恐惧与恶心,正是源于在斯维德里盖洛夫身上看到了自己理论直接后果,从而促使他走向救赎。(关于这位矛盾人物可能会单独出一篇文章随便讲讲)。
他与所有人“相似”,却与所有人“相离”,他意识到所有人的目光将他紧紧相逼,敦促着他的行动与作为,对杀人罪行的恐怖始终笼罩在心头,他时而万念俱灰,时而胆战心惊。当生活有所转机,起色之际他便念起良心的不安,这种窘迫让他必须有所行动,他想逃避,但他同时知晓他无法作出如此没有责任感的行径,于是他时常陷入停摆,正如他在原著中前四部时常如发了发热病一样嗜睡,将自身陷入混沌与沉沦中,试图以此来摆脱不知何处而来的无尽疲惫。
当罗佳走进警察局办公室时,二人的谈话乖离诡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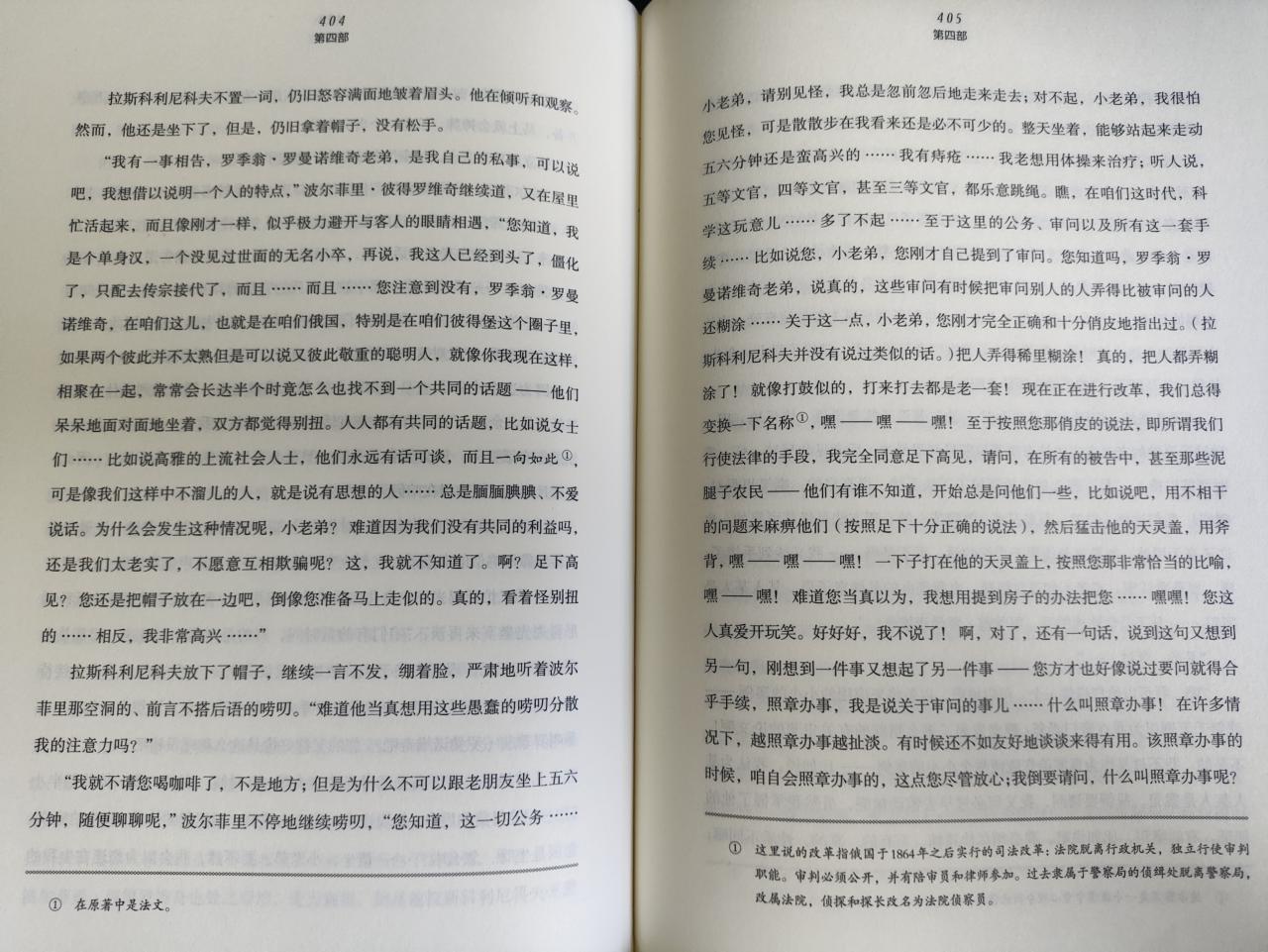
《罪与罚》第四部第五节片段
“......我倒想弄到这么一件罪证,就像二二得四一样确凿无疑!使它成为直接的、无可争辩的证据!"
这里”二二得四“与《地下室手记》中“‘对不起,’他们会向你嚷嚷,‘反对是办不到的:这是二二得四……’”以及浅论加缪荒诞哲学的自由,激情与反抗 - 小黑盒这篇文章中开头引用的句子都有类似的隐喻,这里不一一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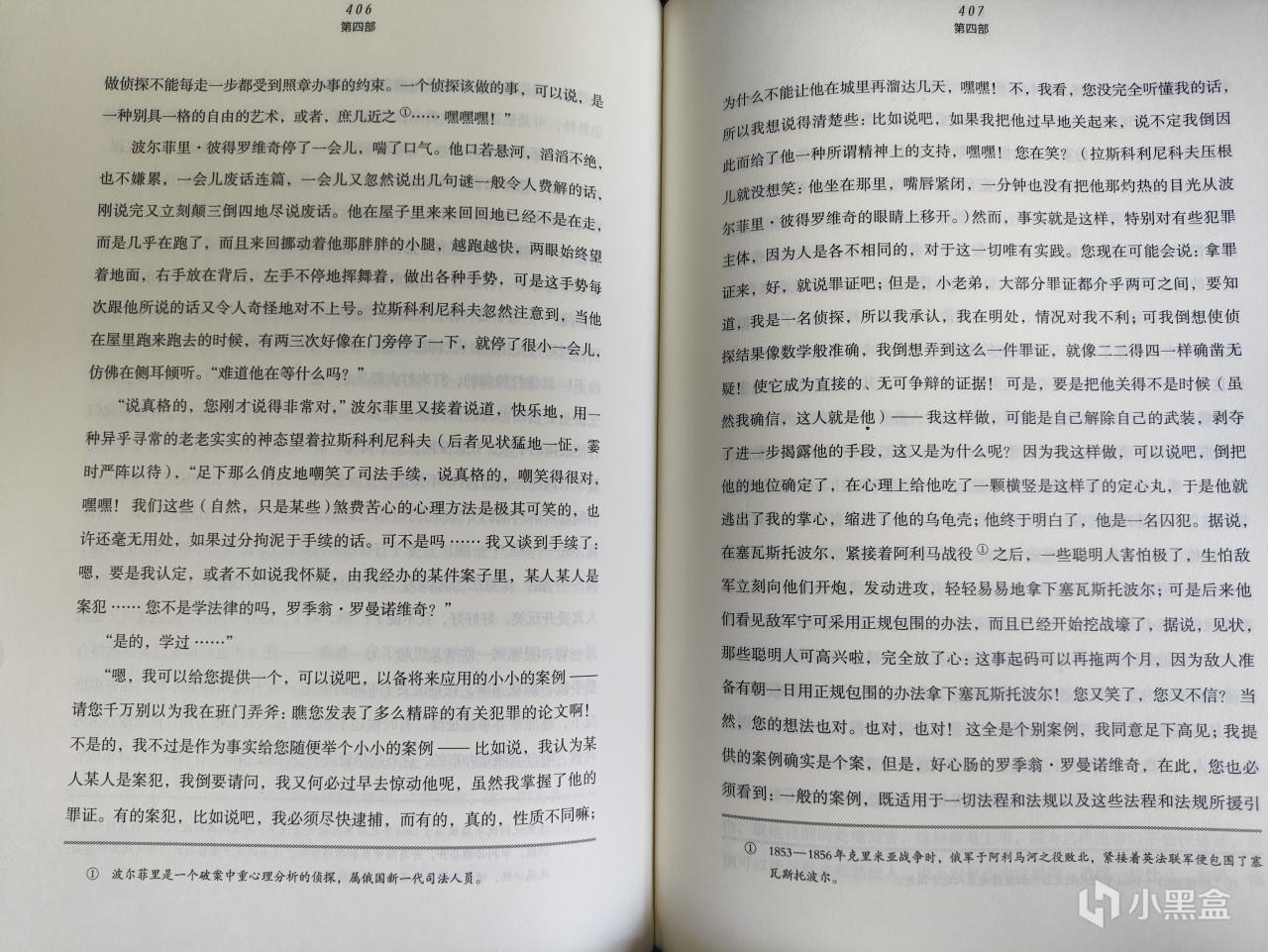
结合后文来看这段侦探“大智若愚”的博弈实在精彩非常
罗佳怀有强烈自首的目的,他以为自己把握主动,明明告诉警察自己是凶手的真相便可直接结束一切,却半被迫地陷入这种似与自己息息相关而天马行空的对话里。他聚精会神,但深感空洞,警察的话语间虽不时回归主题,但又立刻跳开。如同让人处于一种想上课听讲,老师却边吹水边讲知识点的怪诞中,而你必须时刻听着以免错漏,生怕错失”机会“。抑或者说,如同一位早已被有罪的人徒劳地等待着审判。
这种烦躁让人坐如针毡,不由得徒生疲敝。
当读到此处,我不由得地想到了卡夫卡的《审判》里K解雇律师那段,当K对律师产生质疑时,律师通过惩罚商人布洛克,极力地让他心生不该失去如此看似非常珍贵的”机会“。以及《城堡》中找村长七拉八扯,以此寻求目的;误入官员房间听他絮絮叨叨,以此寻求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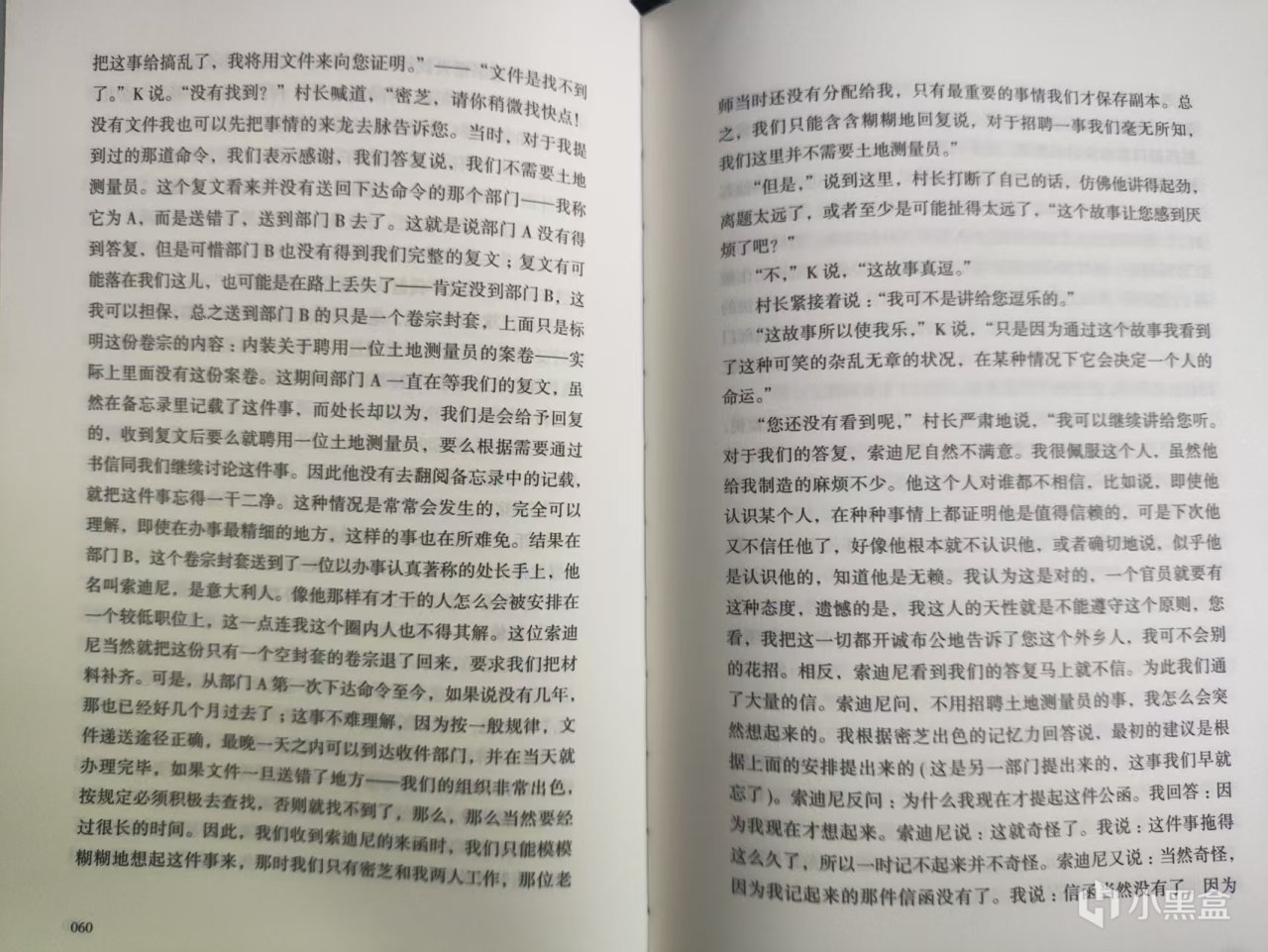
《城堡》第五章片段

《城堡》第十八章片段
(举的例子或许不够贴切,但在涉及这种疲困时的心理刻画时二者之间的联系显然不可轻易割裂)
从这一段我似乎读出了二者表现手法的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片段仿佛形成了某种模糊而熟悉的回声,于是我翻阅《卡夫卡日记》,在这一段似乎找到了关于二者联系的部分线索:

《卡夫卡日记》1914年6月12日片段
这段文字揭示了卡夫卡这两部作品的核心,成为我们透过这种诡谲的表现手法,去真正理解他作品内涵的重要线索。而这恰好也是我之前一篇文章称卡夫卡作品有“他人即地狱”哲学内涵的重要原因。
“孤独、荒诞、异化”,“病态、苦难、救赎”仅仅是理解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切入点,通过阅读陀翁的作品,我似乎寻得了对卡夫卡作品甚至其他作品新的认识:二者对生命道路的叩问和人之存在意义的求索深刻地启迪了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加缪,萨特等人),而对人生目的的探索与和苦修理想的意义的拷问则成为了虚无主义探讨的重要源头。(尼采,毛姆,马尔克斯,鲁迅等人)
有人说,陀翁上承司汤达,下启尼采。就我目前读过的部分尼采作品,我也逐渐开始理解为什么尼采会喜欢他(尼采称其为“唯一能教我知识的心理学家”),原著中的心理刻画与讽刺文笔实在精彩犀利,让人赞叹不已;有些场景刻画得让人身临其境,不尽的细节与修饰不仅不会喧宾夺主、只起到代入的作用,更是为了对场景进行运用,让你置身于人物此时的困境,感同身受。
(诚然,我个人的哲学立场更倾向于尼采的观点,即绝不认同苦修理想,更不寄托宗教救赎;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黑塞《荒原狼》的喜爱,正如尼采对陀翁的赞美)
不过非常惭愧,司汤达的作品尚未读过,不过对于《罪与罚》中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角色我竟有种狄更斯《双城记》里西德尼的形象(或者说《吊带袜天使》第一季里第九集后半部分的ghost-chocola,不是在情爱与善恶,而是单纯从立意上)一样定位的无端联想,实在有趣。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