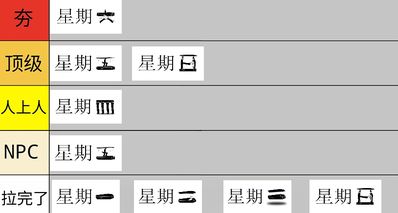2019年5月16日,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與世長辭,享年102歲。他的一生宛若一部現代建築史的絕唱,其作品以非凡的現代筆法對話歷史與文明,留下了無數不朽的傳奇。他的離去,是世界建築界一顆巨星的隕落。
我們在緬懷貝先生對建築界的卓越貢獻、感傷一位大師逝去的同時,或許可以換一個視角,將目光聚焦於他與酒店世界的不解之緣。除了廣爲傳頌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香港中銀大廈和多哈***藝術博物館等地標,貝聿銘同樣在酒店領域留下了深刻印記,例如他筆下富有爭議卻又極具代表性的北京香山飯店,以及四季酒店集團引以爲傲的全球旗艦——紐約四季酒店。不僅如此,他的建築啓蒙源於上海的國際飯店,他位於上海的故居後來變身精品酒店,他甚至曾爲文華東方品牌“代言”,還有一個未被實現的上海和平飯店改造方案。以下,讓我們細述貝聿銘的酒店情緣。

作爲建築大師貝聿銘早期的酒店作品,建於1960年代的丹佛喜來登酒店極具開創性。它被譽爲美國首批現代綜合體項目的先驅,巧妙地將酒店、百貨公司、停車場和公共空間融爲一體。其建築立面窗格疏密有致的設計,不僅在當時極富新意,也使這座建築成爲現代主義的傑出作品.
建築外觀看似輕簡,水泥牆面與窄長玻璃窗的組合卻暗藏玄機。自下而上,窗格由密漸疏,彷彿一首節奏漸緩的視覺詩篇。低處,陽光透過密集的窗欞,灑下靈動詩意的光影;頂端,開闊的窗幅則將“高海拔”的壯麗視野盡收眼底,宛如自然的畫框。這精妙的疏密變化,讓整座建築顯得靈氣十足。


在設計了美國首批城市綜合體之後,貝聿銘於上世紀70年代將其成熟的綜合體模式首次引入澳大利亞。坐落於墨爾本柯林斯大道、佔用整個街區的Collins Place項目,在1975年落成時,其雙塔結構不僅創下了澳大利亞最大單體建築的紀錄。該項目更卓越之處在於其核心的公共空間設計:一個由宏大玻璃頂蓋覆蓋的“溫室公區”(被稱爲“Great Space”的中庭)。這個高六層的下沉廣場,作爲澳大利亞首個採用玻璃空間框架結構的此類空間,成功地將自然光照和通風引入建築核心,巧妙融合了商業零售與公共休閒功能,成爲一個不受天氣干擾、充滿活力的“城市客廳”。其設計理念對後續澳洲建築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Collins Place這一綜合體中,貝聿銘通過對窗框系統的精準把控,來協調不同功能空間的關係。他特意將35號塔樓頂部的15層窗戶設計爲窄長形態,這一處理富含多重設計邏輯:在立面構圖上,它形成了強烈的縱向線條,成爲塔樓頂部醒目的視覺標識,明確了墨爾本索菲特酒店所在的空間領域。在功能上,相較於下部辦公空間更開闊的窗幅,頂部的窄窗爲酒店客房提供了更佳的私密感,同時這種由上寬下窄(頂部酒店爲追求私密性採用窄窗,下部辦公空間爲追求開闊視野採用寬窗,形成對比)的窗幅變化,也微妙地區隔並融合了塔樓內辦公與酒店兩種不同的空間屬性。此外,該項目中兩座塔樓呈45度角錯位,有效拓展了視野,而酒店所在的塔樓平面爲兩個交錯的方形,也提升了空間利用率。

當Collins Place攜墨爾本索菲特酒店投入運營不久,貝聿銘的另一扛鼎之作——新加坡萊佛士城便緊隨其後,破土而出。這座耗費六年光陰雕琢的建築羣,堪稱一件時代的藝術品。其73層的威斯汀史丹福酒店在落成之時,以擎天之勢創下了全球最高酒店的紀錄,不僅刷新了新加坡的城市天際線,更成爲貝聿銘筆下又一枚深刻的現代主義印記。
這座建築最初作爲威斯汀酒店亮相,如今以Swissotel的身份繼續運營。其挺拔的柱形塔身與規整有致的嵌入式陽臺構成了標誌性的建築語彙,這種設計巧妙地平衡了商務所需的嚴謹體面與度假嚮往的輕鬆閒適,使整座酒店能夠在兩種氛圍間從容切換,遊刃有餘。


在貝聿銘心中,香山飯店是他的一份“深情告白”。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建築界沉迷於摩天樓與觀光電梯所代表的“現代化”喧譁與迷思時,他卻選擇迴歸最本真的中國文化基因。他沒有豎起炫耀技術實力的龐然巨物,而是讓建築謙遜地匍匐於香山腳下,通過蜿蜒的鵝卵石徑、靜默的假山池水,演繹出一幅現代版的“曲水流觴”。在極度乾淨簡練的現代主義輪廓下,流淌的是源自蘇州園林的靜謐幽遠和一位遊子建築師化不開的鄉愁。這不僅是一座酒店,更是一次針對時代審美誤區的溫和而有力的啓蒙。

1984年,貝聿銘這件融匯了故園深情的“走心之作”——香山飯店,成功打動了美國建築學會,榮獲其榮譽獎。然而,這項殊榮卻未能撫平大師心中的一絲遺憾。此後歲月,他再未踏足這片傾注了無數心血的山林庭院。並非因爲酒店後來的運作不盡如人意,而是源於一種更爲深邃的審慎。在貝聿銘看來,香山本身的景緻已臻於完美,古木參天,意境天成。他後來曾反思道:“在香山這個樹木啊,水啊,都是很美的……完美得不得了,所以香山這個挑戰是最好不要動它,所以擺一個建築在裏面,我覺得已經錯了。”於是,這座本欲與自然對話的建築,在他心中卻成了對自然美感的一次打擾,成就了一部傑作與憾事交織的複雜傳奇。


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貝聿銘建築藝術的全面昇華期。盧浮宮玻璃金字塔的成功,不僅爲他贏得了普利茲克獎的桂冠,更將其現代主義建築大師的地位推至全球矚目的焦點。藉此東風,他受委託爲當時極具先鋒精神的麗晶酒店集團打造紐約旗艦店。這座旨在“致敬戰前紐約摩天大樓浪漫回憶”的摩天大廈,堪稱其酒店設計的集大成之作。貝聿銘將其標誌性的幾何構圖、對光線的精湛駕馭以及對城市歷史的深刻理解融入其中,使這座建築不僅是功能性的酒店,更成爲一件矗立於曼哈頓天際線的藝術雕塑。該項目的達成,標誌着貝聿銘的影響力從純粹的建築藝術領域,成功延伸至頂級奢華酒店界,成爲其職業生涯的一座輝煌里程碑。

在其全盛時期,麗晶無疑是全球奢華酒店版圖中不容置疑的帝國。它以多元化的先鋒姿態征服了全球最挑剔的旅行家:無論是通過古董建築翻修、都市度假村模式,還是全別墅泳池佈局,其在香港、洛杉磯、巴厘島等地的項目均成爲典範。因此,力邀建築大師貝聿銘於曼哈頓中城打造一座登峯造極的高塔酒店,此舉與麗晶當年志在引領潮流的恢弘氣派完全契合。

紐約麗晶酒店的誕生,始於一個堪稱“黃金三角”的頂級組合:其選址無可挑剔,坐落在麥迪遜大街與公園大道之間的黃金地塊,門戶分設於57街與58街;其設計由建築大師貝聿銘(另有Frank Williams參與)操刀;其背後更有酒店大亨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H. Burns)的鼎力支持,據說當年每間客房的造價就高達百萬美元之巨。如此頂配陣容,讓項目在起點上便成功了一半。
然而,該項目的命運卻並非一帆風順。在它即將開業之際,恰逢經濟泡沫破滅,麗晶酒店集團不得不將其出售。這直接導致這座被寄予厚望、本欲成爲麗晶新旗艦的酒店,尚未正式揭幕便被迫更名爲“紐約四季酒店”,可謂生不逢時。



身處紐約四季的比爾蓋茨、落地玻璃門外就是貝聿銘操刀,由米色大理石和三角燈籠守護的露臺

紐約四季的冠狀雨棚和當年熱衷在此下榻的小貝全家。Joël Robuchon的紐約餐館也曾開設於此

1993年,由建築大師貝聿銘操刀設計的紐約四季酒店在曼哈頓中城盛大開幕,其非凡的設計理念雖贏得業界與公衆的“一邊倒式”好評,但一絲遺憾也隨之而生——因建造初期預算與市場環境考量,一座與之匹配的、足以定義時代的頂級總統套房未能如期呈現。這一未竟的使命,在酒店開業六年後迎來了轉機。隨着酒店被億萬富翁、玩具大亨泰·華納(Ty Warner)收購,他爲這座傳奇建築注入了新的願景。華納力邀當時風頭正勁的設計師彼得·馬裏諾(Peter Marino)聯手,甚至請出已退休的貝聿銘先生親自擔任顧問,共同挑戰一項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酒店52層的天際線之上,憑空打造一個極致的藝術空間。這項宏大的工程歷時七年,耗資高達5000萬美元,最終通過大膽外挑的玻璃觀景臺等設計,成就了名震全球的“泰·華納頂層套房”(Ty Warner Penthouse)。該套房不僅擁有360度全景視野,其冥想室設有瀑布牆,起居室牆壁鑲嵌珍珠母貝,細節極盡奢華與藝術感。至此,在酒店主體落成13年之後,這座貝聿銘酒店的傳奇篇章才終於揮毫寫就了最後一筆,成爲一件真正的“無暇之作”。

貝聿銘事務所曾應文華東方之邀,爲上海地標和平飯店制定了改造計劃。儘管該計劃後因品牌方未能獲得酒店管理權而擱淺,但貝氏提出的“多做加法”原則——即通過增設新元素進行嘗試,若不合適亦可輕鬆移除,而不損傷歷史建築本體——展現了其在歷史建築更新中大膽而審慎的構思。這使我們得以窺見大師對於如何爲經典地標註入當代活力的思考。


如果說貝聿銘的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那麼他設計的酒店便是其中最富人情味的樂章。從香山飯店白牆灰瓦的園林詩意,到紐約四季酒店高聳入雲的現代典雅,再到散落世界各地的匠心之作——無論是赤峯瑞享酒店的幾何光影,還是廣州花園酒店的嶺南氣韻——貝聿銘始終在用空間講述故事。
他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奢華並非材料的堆砌,而是自然、歷史與人文在空間中的和諧共鳴。下榻於他設計的酒店,我們不只是尋找一夜安眠,更是在光影流轉間,完成一場與建築、與自然、也與內心深處的對話。
下一次旅程,不妨選擇一間貝聿銘設計的酒店。在清晨,感受陽光如何透過他精心設計的窗欞,溫柔地喚醒房間;在午後,漫步於他勾勒的庭院,體會“步移景異”的東方美學。你會發現,最好的旅行紀念,正是這些由建築大師爲我們編織的、能夠安放身心與想象的瞬間。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