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为病危的父亲写下了一篇著名的诗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以此赞颂在生命垂暮之时面对死亡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也成了整首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
优秀的诗篇能够穿越时代引起人们的共鸣,2014年由诺兰指导的电影《星际穿越》中也不乏这首诗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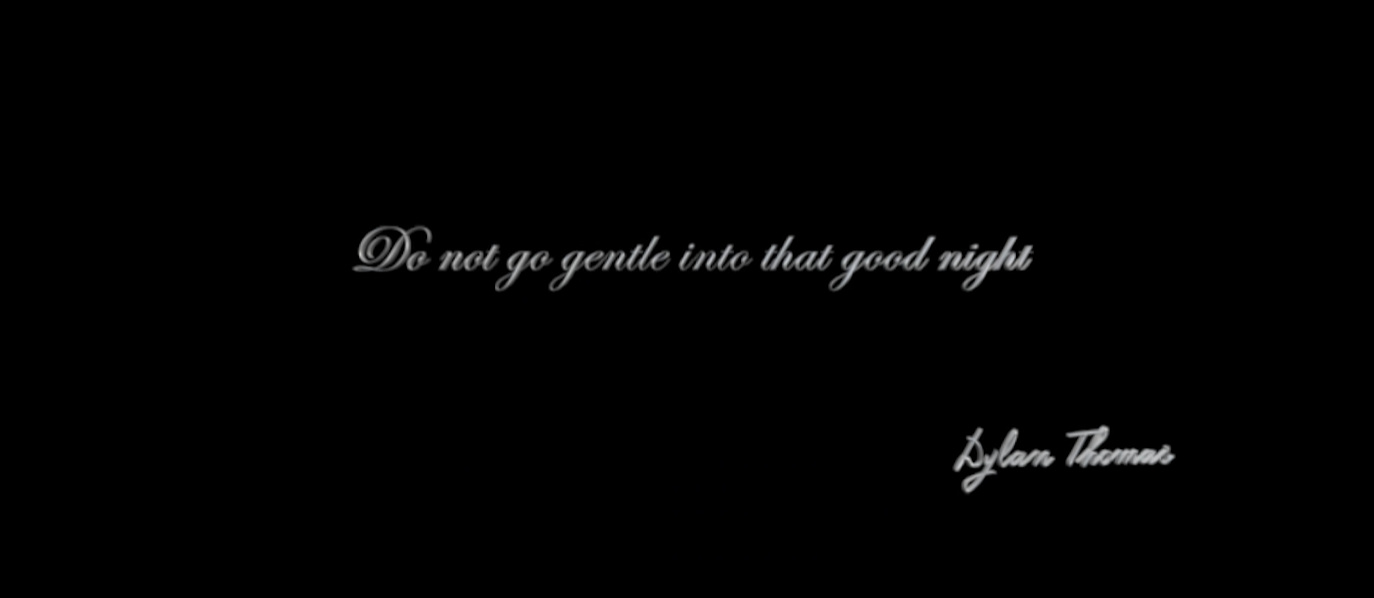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在影片中被多次提及,“良夜”除了死亡与沉寂之外,还隐喻着终将到来、不可违抗的命运以及眼前的危险。《星际穿越》中,人们低头看着脚下这片不再适合生存的土地,抬头看向渐渐落下的夕阳和深邃无边的穹宇。“夜幕即将降临”已经不是床前读物里一句轻飘飘的叙述,而是压在每个人心头沉甸甸的巨石。若夜晚注定到来,至少,影片中的人们选择如何走向它的权利还紧紧攥在手中。
不过,不是所有“夜色”都来得如此鲜明、如此显而易见。许多异变与灾难,往往诞生于无形,却足以致命。温水中的青蛙,也并不知晓自己因何而毙命。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一种荒诞奇特的隐喻将资本主义泡沫中悄然泛出的腐臭气息具象化——格里高尔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只甲虫,但真正被资本异化丧失人情的,格里高尔的家人,却保留了人类的皮囊。被冷漠注视着的格里高尔外表的剧变,成了压垮脆弱亲情的最后一根稻草,金钱与财富,这份早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衡量人际关系的真正标准,此刻才被赤裸裸地拿到桌面上,成为人情谈判的筹码。

然而,若非卡夫卡看似诡谲荒诞的笔触,鲜少有人会去关注,哪怕这种异化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意识的大多数,如同待宰的羔羊,温和地走进了那个良夜……
2016年发售的游戏《INSIDE》,其悲剧内核,也极其相似,它以“内部”为名,将人们引入一场精心构筑的逃亡假象中。作为当年的最佳独立游戏,《INSIDE》的意义,显然不止表面的故事那么简单,其背后的哲学隐喻,也值得人们深思。
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游戏中的小男孩身着一件红色上衣(这压抑的游戏中少有的亮色)在无尽的灰暗中穿行,如同穿透乌云照进大地的一束光,微弱渺茫却仍传递着一丝温暖。只不过从幽暗的自然丛林到冰冷的钢筋水泥,男孩脚下每一步扬起的尘土都浸透着压抑的气息,让这仅存的一点光亮都有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
“光在它将熄的火焰中裹住你。”
——作为光,太孤独;作为生命,太脆弱。

技术在日新月异改造世界的同时,也重构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底层劳动力似乎只有在成为上层的实验品和工具人时才能展现最大的价值,《INSIDE》在无言中将这一点刻画得淋漓尽致,游戏中的压抑气氛也主要来源于此。
所以当我们在小男孩的视角下看到货车运载着一群又一群失去意识的人从树林驶向城市、养殖场白色虫子从成堆腐烂的牲畜尸体中爬出的景象时,才更感心悸。
不要回头,逃亡吧,逃避那些“大人”的追捕,逃避猎狗的围剿,逃避探照灯的扫射,要逃离的事物太多太多,只怕稍有不慎,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成了庞大机器中的一个冰冷的零件。

事与愿违,似乎是被有意地安排过,本该是逃离的过程,却在不断深入这个黑暗的实验,小男孩“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实验与技术的中心、腐败与铜臭的源头——城市。
走过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就如同揭开其中的每一点罪恶。当人们形同傀儡般机械地走进黑暗的房间,只待鲜红的标记赫然出现在冰冷的肢体上——宣告作为流水线产品的合格,整个世界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暗工厂。看着人性与情感沦为被碾碎的齑粉,在机器轰鸣声中被送往垃圾场,才猛然惊觉——技术理性异化带来的渗入骨髓的窒息感早已化作了无形的泥沼,拖拽着每一个步入其中的人,妄想摆脱,只会在挣扎中越陷越深。

诚然,《INSIDE》中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或许只是夸张化地构思和臆想,但无独有偶,早在1853年,爱伦·坡就在其短篇小说《钟楼里的魔鬼》中讲了一个诡异的故事:一个外来者闯入了一个恪守钟楼时间划分生活起居的自治城,致使那一天城中钟楼的大钟敲了十三下,居民们因此像输错代码的程序一样陷入了疯狂……
这种疯狂,归根结底是极致理性中的迷失,对于技术的过度依赖。我们嗤笑他们的荒诞、惊叹故事的离奇,但恰恰,我们最不应该只把这当作饭后消遣的谈资。
20世纪上半叶,工业规模的扩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一部分人开始对技术与理性抱有警惕之心,当时以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发起了对现代工业社会理性的批判。学派的主要著作《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现代工业社会的理性进步过程已经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所谓理性变成了奴役人的工具。
而《INSIDE》的故事,将这种技术理性异化带来的奴役贯彻到底,并在接下来的游戏过程中,让我们见识到:肉体层面的欲擒故纵,只不过是因为灵魂早就被上了无形的枷锁。
楚门的世界

在“城市”中,小男孩穿过2号、3号实验室,最终来到4号实验室,这里的人非常多,但大家已经无心在意一个小男孩的闯入,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振奋,蜂拥到一个大型实验设备的玻璃前议论纷纷。

小男孩钻进了这个实验设备中,看到了培养液中由十余人的肉体聚合构成的白色肉球,他游向肉球,毫无征兆地,被吸收了——小男孩成了由十余个肉体构成的庞大肉球的一部分,并主导着肉球的行动。

它将实验仓的玻璃撞得粉碎,原本在实验设备玻璃外围观的人群四处逃窜。肉球力大无穷,在一路的破坏下,屏幕外的玩家也长舒一口气——之前逃亡时压抑的心情,终于在这一刻迎来爆发:纵使我变成了丑陋不堪的怪物,也要拉着你们一起陪葬。

“被吓傻”的人群有意无意地指引着肉球前进的方向,在坠入一片黑暗后,头顶上突然打下一束如同舞台效果般的灯光,还能听见高处人们的欢呼喝彩声在墙壁间回荡。我的意识仿佛来到了古老年代的炽热午后,目睹斗兽场看台上的贵族们癫狂地嗜着场地中奴隶搏杀后的鲜血,仿佛仅仅用目光还无法饱览血腥的场面。

最终,肉球顺着山坡滚到了野外一束暖阳照耀的草地,并安详地死去,整个故事也划上了句号。
真正令人难受的是,早在之前肉球在实验室中坠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留意到实验场地的微缩模型。肉球最终会滚到那个地方,也在实验预演的范围之内。就连最后那看似温暖的阳光,都渗着算计的冰冷。

以为哪怕死去也好,至少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摆脱了技术带来的奴役。
没曾想,那个追寻自由的本能,一步步将自己推进了深渊。
小男孩一直在逃亡,但自始至终都没逃离实验的掌控。屏幕后的流程与计划书,撕下一页又一页。而这个实验,也在所谓个体的自由意志下,从开始走到了结束。
费尽周折地逃命,也逃不出他人的算计。直到死亡那一刻都未必知晓,这个世界,是“楚门的世界”。

西西弗斯的巨石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无数专家学者对这个命题争论不休。
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罗伯特·M·萨波尔斯基在《决定论:没有自由意志的生命科学》一书中做了相关探讨,这本书由“Turtles all the way down”引入,并以其无限递归类比因果链的无限追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看法:
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因果链向前不断追溯的,但人们误将无法立即追踪的因果确立为自由意志存在的论据。
那么在《INSIDE》这个游戏中,又传达了关于自由意志怎样的看法?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INSIDE》开放式的隐喻中,对于小男孩本身代表含义的解读也众说纷纭,不过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游戏中“控制”、“决定”这些概念是相当具象的。
我们时常要让小男孩戴上场景中的“帽子”来指挥那些无意识的傀儡做出各种各样的行动,来达到场景解谜的目的,这种解谜,在充分展现了游戏这一载体良好交互性的同时,也隐秘地指向了脑中困惑的答案所在。

游戏的隐藏结局就与“控制”有关,甚至是一种打破第四面墙的“控制”。当收集完彩蛋,小男孩来到玉米地下,走向深处,就能看见与控制傀儡有关的发光装置,拔下一旁控制装置的电源,整个游戏也随之结束。黑暗中的小男孩瘫坐在地上,失去了意识,玩家也失去了对小男孩的控制权。

在其他游戏中平平无奇的按键映射,在《INSIDE》中却成为解读作品的又一个突破口。整个游戏中关于控制的解谜,实质上是更深一层的嵌套控制——小男孩的自由意志仅仅是玩家控制下的假象罢了。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从这个角度上看,《INSIDE》的悲剧是层层加码的。
①当我们看到肉球在草地中死去,我们为自由的代价——化成可怖模样后再凄惨地死亡感到悲哀。
②当我们知晓那束看似温暖的阳光,不过是实验室内的灯光,我们为实验预演欺骗性的虚假自由而感到悲哀。
③当我们知晓小男孩自始至终都是屏幕外玩家的傀儡,我们在惊诧中为逃亡本身的荒诞可笑而感到悲哀。
但换一个角度,在无知中逃亡,玩家的意志其实与小男孩的意愿并无差别。追寻逃亡本身的意义时,我们不妨将目光放在对抗荒诞世界的行为本身。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他因触怒宙斯,而被惩罚在冥界中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然而山顶的巨石又注定会滚下,因此这是一件注定没有尽头的重复劳作。

但是,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却这样写道:
“应当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加缪笔下,西西弗斯的幸福,来源于在认清现实的荒诞后,仍能坚持自我意志,不断反抗荒诞的世界。纵使荒诞本身无法改变,但在反抗之时,命运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
从《荷马史诗》到加缪的《西西弗神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存在主义哲学的重构中,西西弗斯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的行为,从徒劳无功转变为了意志超越。
我们再看“玩家-小男孩”这个共轭体,在清醒地意识到技术集权的荒诞世界后,宁愿结束控制也不愿意成为实验祭品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反抗。
——世界何其荒谬,但我们仍能为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
《INSIDE》中藏着一首诗,我想以它来作结再适合不过。
希望在这个”剥削不再是枷锁,而是将人降格为系统最优解参数”的21世纪,我们仍能在西西弗斯式的反抗中,拾起“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的底气。
“pity this busy monster, manunkind,
not. Progress is a comfortable disease:
your victim (death and life safely beyond)
plays with the bigness of his littleness
--- electrons deify one razorblade
into a mountainrange; lenses extend
unwish through curving wherewhen till unwish
returns on its unself.
A world of made
is not a world of born --- pity poor flesh
and trees, poor stars and stones, but never this
fine specimen of hypermagical
ultraomnipotence. We doctors know
a hopeless case if --- listen: there's a hell
of a good universe next door; let's go”
——E.E.Cummings
译:
“不要同情人类这头庸碌的怪兽,
进步是令人舒适的疾病,我们既是发展的受害人,也是罪魁祸首;
我们将生死安全地抛到脑后,以为自己做的事情很伟大,但实际上非常渺小。
电子显微镜下的剃须刀片如山脉般巨大;
望远镜把我们可感知的世界拓展到扭曲的时空,
但人类发现整个宇宙只有我们自己,和过去不同的自己,
一个人类创造的世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初生的世界
——我们可以怜悯那些可悲的肉体以及树木、寒星、碎石,
但绝对不要怜悯这个万能、令人兴奋到极致的标本。
我们医生知道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病例,除非——
听:隔壁就是一个地狱,但却是个美妙的宇宙;我们走吧!”
——E.E.卡明斯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11.23]抢跑冬促,全部百元以下!50款神作佳作史低,黑五大背刺](https://imgheybox1.max-c.com/web/bbs/2025/11/23/79da8f32edf541e2a3772809b439c397.png?imageMogr2/auto-orient/ignore-error/1/format/jpg/thumbnail/398x679%3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