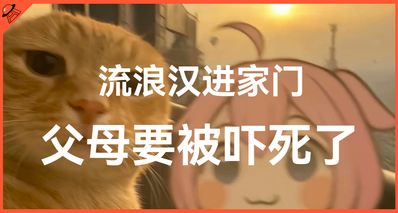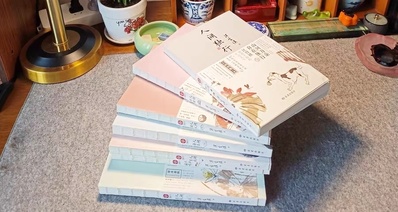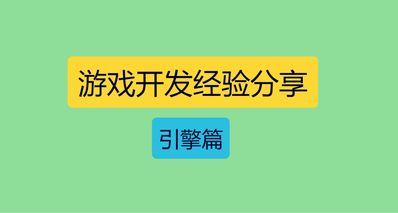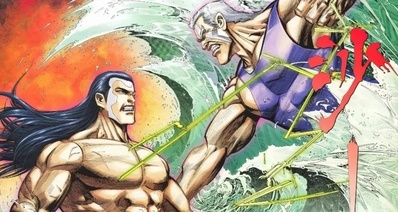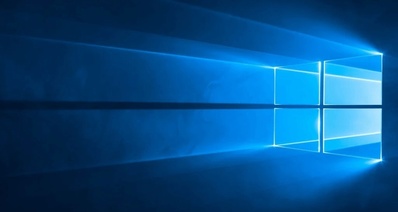说来有些感慨,关于家庭生活的诸多细节,我其实是从汪曾祺的文字里学来的,同样的,也影响了妹妹的写作。
比如“老爷柜”这个词。村里每户人家祖宅的堂屋,正对大门的那面墙前,总要摆一张横贯东西的长木柜。柜上供着香炉、自鸣钟、先人相片,抽屉里珍重地收着红纸和年糕。
小时候总缠着师父问:“到底什么是老爷柜?”师父比划半天,我还是似懂非懂。有次邻居大婶听见了,脱口而出“老油柜”——倒也是,那些涂过清油的柜面经年日久,在白日里看去确实灿灿生光。
最后还是我自作主张下了定义:想必是以前地主老爷们用过的柜子。直到后来读到汪曾祺的散文才恍然,原来就是香案啊!不论供奉的是祖先还是神明,一律尊称“老爷”,这朴素的敬意,竟藏在这样一个寻常的称呼里。
更多时候,汪曾祺的文字像是为那些远去的生活做着详尽的注脚。小时候住在还算热闹的江南乡下,水电时好时坏,煤路更是没有。冬天的热水只有两个来源:茶炉子,或是镇上的澡堂。
每天放学,我都要先回家取两个空水瓶,再去茶炉子打水。每壶两角钱,开水从那个巨大的白铁皮机器里汩汩流出。我一路沉肩提气,小心翼翼地把水提回家,一滴都不洒。妹妹有时会跟在我身后,看着蒸腾的水汽出神。“哥,为什么叫茶炉子呀?”她问。我也答不上来。
直到后来在汪曾祺的书里读到,原来早年的茶炉子主要供应茶客。大屋里砌个炉子,点上四个火孔,坐稳烧水罐,靠粗糠和风箱催旺膛火。那膛火暖着无数个夜里,穿过青石板路的两个小小的影子。
还有师父记在台历边角的菜金账目,总有些奇怪的符号,像没封口的“8”。我和妹妹曾对着那些符号猜了半天,她说像小蝌蚪,我说像打结的绳子。后来又是汪曾祺告诉我们,这叫苏州码子。
那天我指着书对妹妹说:“看,我们猜了半天的谜底。”她凑过来,盯着那几个字,就好像我们共同守护了一个很久的秘密。
说来也怪,我对汪曾祺总有种没来由的亲近。在他的文字里,我能在饺面店遇见他,能在晚茶时分的烧饼摊前与他并肩站着,买两个刚出炉的糖烧饼,还能在端午的乡村里,跟他一起剥着高邮的咸鸭蛋。
师父离开得突然,走时片字未留。但每当我翻开汪曾祺的书,那些逝去的生活便又活了过来——茶炉子的水汽,老爷柜上的烛光,汪曾祺把这些都写了下来,而我们则把它们活过一遍。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