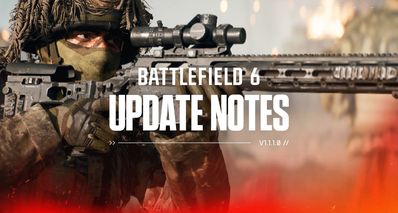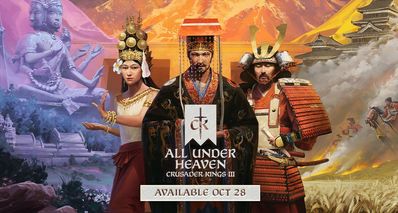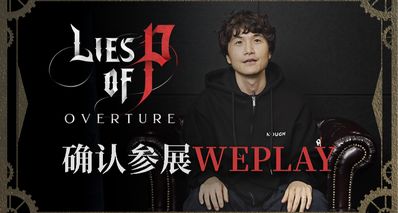终有一日,今天的未知之谜会得到解开,但那需要漫长的勤勉研究。人类寿命有限,一个人穷尽毕生之力也不足以攻克天空这如此巨大的课题。…因此,唯有经过岁月和持续数代的研究,此等知识才能逐渐显现。终有一日,我们的子孙会惊讶于他们的先人竟不了解那些无比浅薄的常识…待到谜团揭开之时,我们早已被遗忘。如果宇宙无法为人类世代提供无穷无尽的谜题,那它就实在太渺小,太可悲了…大自然不会一下子彰显它的全部奥秘。 ————塞涅卡,《自然问题》卷七,1世纪
如果说到太空游戏,那么我想一定绕不开一款游戏——群星。


Hello,Stellaris!
《群星》(stellaris)是一款宇宙探索和帝国建设的大型4X策略游戏,由Paradox Development Studio开发。玩家在游戏中选择或创建一个星系文明,通过探索、扩张、开发和征服来管理和扩展自己的星际帝国。游戏特色包括宏大的宇宙场景、复杂的策略与管理系统、丰富的外交和战争机制,以及深度的种族和科技树定制。
作为一款老少咸宜的合家欢游戏,群星的新手引导完备,入门轻松。

快速上手
而拥有崇高道德观与价值观的第四天灾们也使得群星的美名从太阳系到半人马座阿尔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以上都是反话()
当然,对游戏复杂的操作与令人眼花缭乱的系统来说,一百小时的笔者也只是堪堪入门,便暂先按下不表。
进入正题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为什么打开群星吗?

群星,启动!
我还记得那是三四年前,第一次从欧陆风云4的水群中听说这个游戏。据传也是一款穷兵黩武的战争模拟器,便主动去搜了搜,可惜的是当时封面上的STELLARIS着实让只认识STAR的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而介绍上的图片也少了传统填色的色块,我就这样第一次离开了它。

三体三部曲
直到后来,刘慈欣的《三体》在我们班里红极一时。当我看到一切都在程心的微操结束后,我突然想,如果人类能更强大一些,如果我能成为人类的“执剑人”,当然我是说如果——于是这时我再次想起了那个难记的名字,《Stellaris》。
我想,这真是贼老天再给人类的五百年,于是我便迫不及待地微操起人族。

电令太阳系舰队左移5千米
游戏中的种种操作我就不细数下去了,无论是人类的地球联合国还是人类联邦,两者都让我过了一把瘾。

人联

地联
没错,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直到半夜两三点我才反应过来,或许我该明天再踏上这段征途。于是就在我熄灯之后,准备拉上窗帘,却不经意地望向了夜空,我发现,即便是宇宙的深邃黑暗好像也只昭示着一件事——群星,它们就在那。
人类为什么望向群星?
一、好奇心与为什么
好奇心的历史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
好奇心是植根于人类本质中的一种强大推动力,它不仅驱动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探索和客观认识,而且是促进科学发现、技术创新、文化多样性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人类对于外界的每一项客观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都植根于好奇心的激发和满足过程之中,它引领我们质疑既有知识,勇于挑战未知,促使我们不断扩展认识的边界和深度。

没有科学家的飞船无法行动
正如没有科学家的科研船无法调查,没有好奇心的人类怎么能认识群星呢?
宇航员:好的休斯顿,我们开始打开1号和3号
指挥中心:然后我们会一起跟进辅助的动力单元的开启
指挥中心:呼叫哥伦比亚,氢燃料温度状况今天不列入必检项目…我们一会大气层见
飞行员:收到休斯顿,氢燃料温度状况无需检测,我们进入大气层
指挥中心:Rick,我们可不是想误导你,可别忘了写在手册3-44页上的东西
指挥官:好的我们马上检查,我们打开了飞行控制系统的电源并且正在认真的进行接下来的事情
指挥中心:很好,指挥中心:呼叫哥伦比亚号Rick,这里是休斯顿,我们请求再进行一次27号项目
指挥中心:休斯顿呼叫哥伦比亚号,收到请回答
指挥中心:休斯顿高频呼叫哥伦比亚号,收到请回答......
1981年,哥伦比亚号成为首个进入地球轨道飞行的航天飞机,并在二十多年内成功完成了27次任务。在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及其船员在16天内旅行了超过六百万英里。但在预定着陆前16分钟,航天飞机的毁灭显示了太空飞行仍充满巨大风险,这种风险必须被认识到,但永远不能被消极接受。七位哥伦比亚号宇航员相信这种风险是值得的。
我们所惧怕的生命消逝的那天,实则为永恒的开端。——卢修斯,《短暂的生命》
他们带着伟大的探索精神与人类赞歌般的勇气挣脱了大地,一齐投入了群星。
我们不知道更早的人类会不会在每个夜晚眺望着浩瀚无垠的星空,但我们知道,我们在向宇宙索要“为什么”的答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不会停下脚步,因为群星就在那里。
二、它们是谁

星系团SMACS0723
2022年7月12日,NASA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了迄今为止最深、最清晰的遥远宇宙红外图像,揭示了星系团SMACS0723的细节。这张照片显示了数千个红外线中最微弱的星系,覆盖了宇宙中一片广阔的区域,其细节之丰富令人惊叹。通过12.5小时的观测,韦伯的NIRCam捕捉到了约46亿年前形成的星系团,揭示了以往未见的微小结构,包括星团和漫射特征。
一个远在40亿光年外的,渺小行星上的土著居民们第一次见到了他们从未真正认识过的宇宙。

船底座星云NGC3322的“宇宙断崖”
或许是好奇心作祟,于是我们迫切的想要更加认识“它们”一点,哪怕只多一点,也足以让我们欣喜若狂,因为我们迫切的想知道,想了解“它们”,“它们”不止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美丽的宇宙。
三、我们是谁
寻找身份认同从来都不是觉醒的人工智能的专属,人类也从未停下寻找“我们是谁”的群体身份认同的脚步。
“在他者的凝视下,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主观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客观的‘物’,一个被评判和观察的对象。这种被他者凝视的体验,迫使我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从而在自我认同的构建过程中,他者的凝视成为了一面镜子,映照出我自己。”
他者的存在和凝视,不仅仅揭示了自我作为对象的一面,而且还是个体自我认同和自由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他者的目光,个体不仅看到了自身的局限,也看到了超越这些局限的可能性,从而在自由和责任之间寻找自我的意义和位置。
所以不止是为了探索与冒险,寻找外星生命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在主体建构自我的过程中,他者的“凝视”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者的“凝视”促进了个人的自我形象的塑造,对我们寻找“我们”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四、他们在哪
“人们否认了外星文明的存在,因为,如果外星文明真的存在的话,应该会发生两件事情:一是它们应当拜访过地球了,二是它们应该向我们发出过一些它们存在的信号。”——费米

游戏中的外星生命
费米悖论起源于20世纪中叶,由意大利裔美国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提出的一个简单却引人深思的问题:“他们在哪里?”这个问题指向了一个看似明显的矛盾:鉴于宇宙的广袤和年龄,以及众多可能适宜生命存在的星系,理论上应该存在大量的外星文明。
不同于游戏中的外星势力的随处可见,我们至今未能发现任何外星生命的明确证据,这一事实与潜在的外星文明众多的预期相悖。
费米悖论的核心在于宇宙的可观测规模与外星生命尚未被发现之间的不匹配。天文学家估计,仅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就有上百亿颗可能拥有类地行星的恒星,而银河系本身只是宇宙中数千亿个星系之一。在这样浩瀚的数字面前,即使只有极小比例的星系拥有发展高级文明的条件,我们也应该能够观测到某些迹象,比如无线电信号或其他技术遗迹。

德雷克公式
针对费米悖论,科学界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尝试解释这一缺乏外星接触的现象。这些假说大致可以分为几个类别:
稀有地球假说:认为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发展到智能文明的条件极其罕见,因此宇宙中极少有类似的环境能够孕育出发达的外星文明。
大过滤器理论:提出在生命从简单形式向复杂、智能形式演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碍(滤网),这导致智能生命非常罕见。
启示录假说:认为高度发达的文明最终都会遭遇自我毁灭,无论是通过核战争、环境破坏还是其他方式,因此他们存在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暂,难以被其他文明观测到。
动物园假说:外星文明确实存在,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选择不与地球文明接触,将地球视为一种保护区或实验室,避免直接干预。
技术发展差异:即使宇宙中存在其他文明,它们的技术发展水平可能与我们大相径庭,我们可能无法识别他们的通信方式,或者他们已经超越了使用我们能够检测的技术。
当然,对于费米悖论的假说还有很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举例了。
我们对生命的追求就像是对我们自己的追求,在数不清的年月前,我们从大海与滩涂中走出,在1.49亿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由徜徉。我们变换着身形,最终用6000亿亿亿个粒子成为这个世界主人,一切只为了我们的生命与种族能在这颗45.4亿岁的小小的岩石行星延续。我们渴望着能与我们对话的世界,我们渴望不再孤独。
五、暗淡蓝点
再来看一眼这个小点。就在这里。这就是家。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小点上,每一个你爱的人,每一个你认识的人,每一个你听说过的人,每一个人,无论是谁,都在此度过一生。我们所有的快乐和挣扎,数以千万自傲的宗教信仰、思想体系观念意识,以及经济学原理教义,每一个猎人或征服者,每一位勇士或懦夫,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或摧毁者,每一位君王或农夫,每一对陷入爱河的年轻伴侣,每一位为人父母者,所有充满希望的小孩、发明家或探险者,每一位灵魂导师,每一个腐败的政客,每一个所谓的‘超级巨星’,每一个所谓的‘至高领袖’,每一位我们人类史上的圣人或罪人……我们的一切一切,全部都存在于这样一粒悬浮在一束阳光中的尘埃上。——卡尔·萨根,《暗淡蓝点》

旅行者1号拍摄的著名地球照片《暗淡蓝点》

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发布的新版本“暗淡蓝点”图像

游戏中的人类
你是什么时候察觉到自己的渺小呢?
是第一次从可观测宇宙的879,873,000,000,000,000,000,000千米直径中找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个零?
还是在可观测宇宙粒子数的1的后面的80个0中看见了自己?
宇宙是时空的深渊,我们从深渊中窥视着迷蒙的未来。人类经历过于地球的渺小,也会继续经历于宇宙的渺小,但我们始终不会停下脚步。

1975年列昂诺夫在联盟19号内
1965年3月,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在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太空行走的惊险旅程之后,回到了宇宙飞船的避难所中。在那里,他用手中的彩色铅笔,捕捉了一个宏伟场景——太阳自地平线上升起,洒下红橙黄蓝的光辉,仿佛是对他壮举的静默赞歌。八年后的1973年,他将这一刻的记忆转化为画笔下的艺术,一套以此景象为灵感的画作被印制在明信片上,遍布世界各地,激励着那些仰望星空的人们。

我们就像在游戏中关闭了胜利年份的人类,谁也不知道我们能玩多久。
于是在未知的宇宙中,我们迷茫,我们思考,我们的未来无限;我们渺小,我们好奇,我们终将向着群星伸手,朗声欢笑。
我们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宇宙局部的体现。我们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起源冥思苦想:星辰的产物也在思索繁星;千亿亿亿个原子构成的有机集合体正在思考着原子的演化;沿着漫长的旅途,至少在这里,意识觉醒了。我们的忠诚是对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我们为地球代言。我们的生存义务不只属于我们自己,而且属于整个宇宙,古老广袤的宇宙,我们的生长之地。
————卡尔·萨根,《宇宙》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