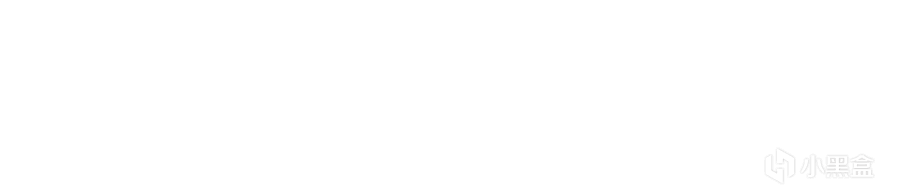
乾了這碗子母河水,我保你今夜就能懷上鬼胎。
1.
這件事發生在五年前。
在經歷了一場無妄之災後,那時的我和丈夫十分渴望重新擁有一個孩子。然而由於那場突如其來的厄運來得太過猛烈,我在悲痛之餘患上了子宮肌瘤——這也就此封殺了我僅存的一絲希望。
啊啊,老天爺對我太殘忍了。那時的我如此想到。
失魂落魄之際,丈夫說:我們去散散心吧。
我時常會在電視上看到XX省播放的旅遊廣告。畫面中的一家三口看起來真開心。爸爸,媽媽,還有他們那可愛活潑的孩子——扎着麻花辮,穿着白紗的蓬蓬裙,她的眼睛是圓而亮的,笑起來臉上有兩個小酒窩——看起來就像,就像——
我的內心悲哀地嗚咽了一聲。
擺脫了車水馬龍,林立的大廈如行道樹般向後退去,輪胎碦拉碦拉軋在碎石塊上,穿過淺灘和戈壁,我們從黎明駛入黃昏,又從黃昏駛入黑夜。兩個可憐的傷心人靜悄悄地碾過這個世界廢棄的影子,遊魂般地向着目的地飄蕩而去。
我們將車停在一棵老柳樹下,沿着崎嶇的山路徒步向上,每走幾步便能看到一處指示標。臨近登頂,我們便聽到清脆的、河水奔騰的聲音。站在山頂向下看,翠綠色的河就如一條流動發光的綢帶。
一個瞎眼老人坐在坑坑窪窪的磐石上,手裏拿着一塊“歡迎住宿”的牌子。他將下巴杵在牌子上,似乎在打瞌睡。老人旁邊站着個十歲上下的男孩,那孩子怯生生地打量着我們,操着一口並不標準的普通話問:“叔叔阿姨住宿嗎?”
丈夫轉身要走。可我實在不忍心拒絕,想着反正也累了,不如就找個地方歇歇腳。我拉住那個孩子的手,男孩推推老人,老人睜開一雙無神且白濁的眼睛,接過男孩遞來的柺棍,領着我們顫巍巍地向民宿走去。
宋仙河位於兩山之間,河上懸着一座老吊橋。我抓着橋邊的麻繩,一刻都不敢鬆手。那老人雖盲,卻能在隔着縫隙的木板上走得又準又快。橋下河水滾滾,部分撞碎在已然失去棱角的磐石上,衝激出一些渾濁的白沫。從橋上遠遠望去,只覺得青山茫茫,幾隻山雀掠過水麪,向着遠方的碧空逍遙而去。
過了橋,又沿着陡峭的石壁小路摸着繩索向下,我們終於來到了對岸的簡樸民宿。屋子不大,設施卻很齊全,藤木傢俱整齊地陳列在其中,順着榆木樓梯爬上去,二樓便是供人住宿的三四個房間。
我們的房間在最裏側,從窗戶向外看去,正好能看見那條奔湧的宋仙河。
臨走前,老人囑咐我們:
“下午記得去看求子哦。”
2.
下午天色漸陰。一排女人捧着一條紅色長巾,站在宋仙河邊。
戴着紅冠子的長者揮起鼓槌,重重地擊在羊皮鼓上——咚、咚、咚。敲了三下,那排女人便齊刷刷地跪下來開始哭。長者模樣的人用方言喊道:“大點聲!不然河仙嬤嬤聽不見!”
她們哭了不知多久,又聽方纔敲鼓的人大喝一聲,女人們便止住了哭聲。一羣不知從哪兒來的山雀盤旋在她們頭頂,大約繞了三圈後便哄散而去。
然後我看見民宿那家的小男孩,他頭頂一塊長木板,晃悠悠地走了過去。那塊木板上放着約莫十三四碗水。水面晃晃蕩蕩,幾乎快要溢出來。
我踮起腳往前看,那水顏色渾濁,有一碗上還浮着一片不知是落葉還是水草的東西。擊鼓者將碗一一端給那羣女人。其中一個湊到碗邊聞了聞,便彎腰乾嘔起來。其他人的臉色也變得難看,她們看看那碗水,又面面相覷,最後狠下心來,一個個捏着鼻子往嘴裏灌。
最先喝完的女人面向宋仙河跪下,用手捧着河水不停地往嘴裏送,那樣子我看着一陣犯惡心。
傳說,宋仙河是一條求子河,只要喝一口宋仙河的水就能夠懷孕。因爲宋仙河裏住着河仙嬤嬤,河仙嬤嬤可憐那些女人,便會把孩子送去前來求子的夫妻身邊。
我看着她們,眼淚突然就掉了下來。
待人羣散去,我將手伸進宋仙河裏。我聞到一股淺淺的腥味——大概是腐爛的水草、魚蝦的粘液、河牀的淤泥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不知爲何,我突然聯想到了羊水——母親子宮裏溫暖的、能夠孕育一切的羊水。
我感受到那裏好像有生命存在——在溫暖的羊水中,彷彿有一隻冰涼的小手正在觸摸我的手。
當晚我側躺在牀上,窗外起了很大的霧,遠方連綿起伏的山巒也被籠罩其中。風吹得窗子啪嗒作響,一兩隻飛蛾撞向燭燈,鍥而不捨地尋死。而就在我睡眼朦朧間,有羣影子正在霧裏行走。他們小聲嗚咽着,依依不捨地向着宋仙河中央走去。
3.
第二天醒來,陽光很好。
民宿家的那個男孩正在二樓掃地。他太瘦了,那件寬大的短袖掛在他的身體上晃晃悠悠,像個晾衣杆。我問他,你多大了?他說,十五。我又問他,喫飯了嗎。他點點頭,喫了,喫的稀粥就窩頭。我捏了捏他棍兒似的胳膊說,就喫這些嗎?他想了想,不好意思地笑了,還有一碟鹹菜。
他臉上有一處胎記,很大,幾乎覆蓋了整個太陽穴。我從揹包裏拿出兩塊巧克力給他。男孩小心翼翼打量食物的樣子刺痛了我。
我問他叫什麼。他說他叫地生,土地的地,生活的生。末了又補充一句,也是花生的生。
這時,瞎眼老人回來了。他拄着柺棍,狠狠地搗了下地,地生一哆嗦,拿着掃把下了樓。
瞎眼老人睜着一雙泛白的眼球,對着空氣咧開嘴咯咯咯地笑了。他問我們,去看求子沒有?我說,去了。他說,放心,一週後還有更好玩的。他拄着柺棍不緊不慢地上樓,與我們擦肩而過時,又說:“起霧之後,就不要再出門了,要是看見什麼東西,就當做沒看見吧。”
地生老老實實地打掃乾淨客廳,不知從哪裏偷偷摸出一把乾花生塞給我,然後便又穿上求子那天的行頭出了門。
我和丈夫順着民宿後面的青苔小路走去宋仙河畔。求子儀式依舊在進行,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夫妻們站在河畔,祈求着擊鼓之人能贈與一碗宋仙河水。又一陣鬼哭狼嚎之後,地生又一次晃悠悠地頂着板子送上十幾碗水,整個流程跟昨天如出一轍。
一隻山雀立在磐石上,看着這場荒唐的鬧劇,咕噥着嗓子叫了幾聲。
晚上回到民宿後,我們邀請地生一起喫飯,可他卻只知道盯着餐桌中央的那碟鹹菜下筷子。我使勁地給他夾肉,興許是面對別人的好意有些惶恐,他始終有些不知所措。於是丈夫又掏出幾塊巧克力,地生見了,兩眼冒光地接過去,小聲地說了謝謝。
我問地生,你是每天都要去那個儀式幫忙嗎?地生說也不是,上一個端水的掉進河裏淹死了,所以他就臨時負責去端,能賺點外快。我又問他頂着那塊板子的時候重不重。他說重,但是水一定不能灑出來,不然一天的收入就沒有了。
我問他和瞎眼老人是什麼關係。他說他沒有別的親人了,只有這一個伯伯。突然,那瞎眼老頭不知又從哪冒了出來,嗓門洪亮地叫着地生的名字。地生急忙應了一聲,起身就往樓下跑去。
他起身的時候,褲腰處露出來一小塊乾癟的皮膚,上面佈滿了淤青。
4.
第三天早晨,地生突然急匆匆地來敲房門。
他說我們今天最好待在民宿裏,不要出去看熱鬧。我一頭霧水,問是什麼熱鬧。但他只是撓了撓頭,支支吾吾地走開了。於是,我和丈夫喫完早餐後就一直留在大廳。瞎眼老人躺在搖椅上曬太陽,輕輕哼着一種古怪的調子。他嗓子裏像憋了一口痰,聲音像一支斷了弦的二胡在垂死掙扎。而我只聽清了兩句話:
送骨入土,送魂還江。
“今天要請河仙。”他看向我說,“請的時候要宰牛羊款待河仙嬤嬤,尤其是那些來求子的夫妻,必須親臨現場。”說着,他又咧開一口燻黃的牙,“去河邊看看吧,他們現在應該正殺畜生呢。晚上記得早點回來,別在外頭亂晃。”
今天的宋仙河風平浪靜。河邊圍滿了烏泱泱的人,一個光膀子的壯漢正在石頭上磨刀。一隻羊認命地躺在推車上,它旁邊還躺着一隻公雞,一頭牛,還有幾條魚。推車旁放着幾隻木桶。
那壯漢磨完刀,單手將羊頭拎到木桶上,捏着羊脖,狠狠地給它來了一刀。那隻羊發出一聲尖利而悽慘的哀叫,便不動了。
血放了多半桶。那壯漢拎起羊扔進宋仙河中,然後是雞、牛頭、牛腿,最後是魚。河畔驀地颳起一陣風,夾雜着血腥氣味往人臉上撲。幾個男人抬着一大口香爐來到河邊,一些當地村民拿着點燃的香燭插進爐灰裏,又對着鞠躬拜了拜,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又一羣人護送着一輛卡車緩緩駛來。卡車後座載着幾個吹嗩吶的,他們坐在後座兩側,中間擺着幾個摞在一起的木盒子。
前來看請河仙的觀衆裏,有當地村民,有暫時歇腳的卡車司機,也有外地遊客。當主持這場儀式的人大喊了一聲“跪——”,他們便整齊地跪下。我也拉着丈夫一起跪了下去。
鼓點漸漸開始急促起來,主持儀式的人左搖右擺,用方言大聲哼唱着什麼。這時河上緩緩駛來一艘船,主持儀式的人剛一上去,鼓點就變得愈發緊湊,嗩吶和鑼聲也越來越大,似乎在掩蓋什麼。
我隱隱約約聽見有人哭——有低聲啜泣,也有大聲嚎啕——還有類似於……有人在趟着水行走的聲音。
“閉眼——”主持儀式的人大喊。
我們照做。過了不知多久,我悄悄睜開眼睛。
那些木盒空了,橫七豎八地散落在河邊。那艘船載着主持儀式的人向着河中央駛去,而在船的周圍,許多小小的漩渦正隨着船隻移動。船身被一團白茫茫的霧包裹起來。我依稀能看見許多溼漉漉的人正趟着河水跟船走,行動的速度很慢,頭是低垂的,看不到表情。
我聽見主持儀式的人喊了一聲“他們跟上來了”。
5.
那天的請河仙儀式結束時,我依舊是迷糊的。
我問丈夫有沒有看到那羣溼漉漉的人。丈夫迷惑地搖頭,說沒有,自己剛纔一直閉着眼。
幾隻山雀返回巢穴,緊緊地擠在一起,眯着眼休息。風吹過山谷,帶起隆隆的迴響。長滿青苔的小路上,人們三兩結伴地走着,我和丈夫跟在人羣后面。我不時回頭望着早已恢復平靜的宋仙河,一陣怪異感湧上心頭。
回到民宿的時候,地生已經把飯做好了。他給我們煮了一大碗麪,裏面加了兩個荷包蛋,還有很多的肉沫,而他的晚飯依舊是饅頭鹹菜。我們喫飯的時候,瞎眼老頭就在櫃檯後罵罵咧咧,說地生這個敗家子,還有錢請別人喫肉。我問老頭,你不是眼睛看不到嗎?他說,我能聞出味兒來。
等喫完飯,我告訴地生今天去看了請河仙,還告訴他我看到了那羣河中央溼漉漉的人。地生聞言,倒也不很喫驚。
我問他,爲什麼有人會在河裏,那也是請河仙的一部分嗎。
地生說,你就當什麼都沒看見吧。
當晚,我莫名其妙地發起了高燒。丈夫說我當時兩眼發直,呆愣愣地盯着窗外,眼底發青,臉色發白——那是一種死人的狀態。
丈夫找來瞎眼老頭和地生,問附近有沒有醫生。老頭說沒用,但他光聽丈夫的描述,大概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丈夫說,地生當時很着急。他從兜裏拿出我們之前給他的巧克力——這個傻孩子從小到大沒見過巧克力,覺得它甜還好喫,便把它當成了靈丹妙藥,想讓我補補身子。聽丈夫說巧克力根本派不上用場,要喫藥纔行,那傻孩子又急匆匆跑出去給我找藥。
瞎眼老頭找了一隻生雞蛋,又拿了一面鏡子。他把雞蛋握在手裏,又將拳頭放在鏡子上,嘴裏陸續唸了幾個名字,直到唸完最後一個名字後,他突然將手鬆開,只見那顆雞蛋便直挺挺地立住了。
丈夫問他,你剛纔唸的那個名字是誰?
老頭的眉毛擰成一個叉號,他說,我剛纔唸的是一個死人的名字。
丈夫又問,這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老頭當時臉色有些不太好看,只說了一句,有東西盯上她了。
丈夫告訴我,那天他一個大老爺們快被嚇哭了,因爲那個老頭後來一邊搖頭,一邊告訴他準備後事吧。他還以爲我沒救了。結果守了我一晚,等到白天,我又沒事了。
清醒後的那天是我們來到宋仙河的第四天。
也就是在那天,地生的屍體在宋仙河不遠處的小池塘裏被發現。
6.
地生被撈起來的時候,全身被泡得發白發脹,像一隻鼓了氣的蛤蟆。瞎眼老頭守在屍體旁,一隻手捂着地生的臉,不停地嘆氣,一雙渾白的眼睛望着虛空發呆。
對於地生的死,時至今日我仍有愧疚。他是爲了給我找藥才掉進池塘裏淹死的。
地生的屍體被拉去當地的鎮上火化時,我去送了他最後一程。我眼看着他腫大的身子被送進焚化爐裏,再推出來時,就變成了幾塊骨頭,還有一堆灰。
地生的骨灰被收在一個陶瓷罈子裏。我們問剩下的那些骨頭能不能一併帶走。工作人員說當然可以。
回去的路上,瞎眼老頭抱着地生的骨灰,依舊望着虛空發愣。這下,本就不大的民宿便徹底只剩下他一個人了。瞎眼老頭將罈子擱在櫃檯的最上頭,蹲在地上嗚嗚地哭。我掏出一千元整的現金塞給他,他收下了,抹了抹淚,說:
“我們地生是替你去死的。”
晚上我怎麼也睡不踏實。一想起地生,我就掉眼淚,於是便一個人來到民宿後院的陽臺上發呆。宋仙河靜靜地流淌着,皓月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一陣風吹過來,影子就被吹碎了。山裏晝夜溫差大,我身上披了條厚毯子,可還是覺得冷。
藉着昏暗的月光,我隱約看到宋仙河邊有一個人影。人影正抱着什麼東西往河裏撒,一邊撒嘴裏還一邊呼喚着。我壯着膽子,拿着手電筒從小路偷偷摸過去。那是瞎眼老頭,他手裏正抱着地生的骨灰罈,將地生的骨灰撒向宋仙河。
地生——回來了——地生——回來了——
如果當時你也在場,那大概會是你聽到過的最毛骨悚然的聲音。我躲在一棵樹後,不敢發出半點聲音。一隻山雀落在我腳邊,不解地歪了歪腦袋,叫了一聲。老頭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一直到他的聲音啞得不成樣子。
我悄咪咪地看去,只見那老頭興許是怕骨灰撒得不乾淨,還把罈子在水裏涮了涮。
突然,河中央出現了一團白霧。
我想起來了,這就是我在求子儀式裏看到過的那種白霧。
白霧裏先是出現了兩三個模糊的人影,然後是四個、五個、十個……影子越來越多,並緩緩地開始向着河岸移動。我心中突然湧起一種不祥的預感,便顧不得那麼多,衝上去拉着瞎眼老頭就往回跑。
我又背又抱又拖又拽,好不容易把那老頭弄回民宿。鎖好門窗後,我叫醒丈夫,告訴了他剛纔看到的一切。老頭還挺生氣,對我罵罵咧咧,說你把我弄回來幹啥,我們地生的骨灰罈都落在河邊了。
我也生氣,說你還真是狗咬呂洞賓,剛纔河裏出現的那東西你看不見,可我能看見,我不管你,難道要留你在那裏等死嗎?
老頭問,什麼東西?
我便又把我看到的複述了一遍。
老頭沉思了一會兒,說,有些事情,讓你們知道也無妨。
7.
宋仙河坐落於山區,從南向北流過宋村中部。靠山喫山靠水喫水,那時的宋村靠着這條河將漁業發展得蒸蒸日上。
直到2001年的夏天,一場突如其來的山洪,將寧靜的一切砸了個粉碎。
有還沒弄明白怎麼回事,就在睡夢中被水沖走的;也有老人小孩腿腳不利索,沒跑幾步就被洪流攆上的;還有人試圖往樹上爬,結果連樹也被沖斷的……
洶湧如虎的山洪卷着數不清的房屋人畜流向宋仙河。待洪水褪去,一具具又漲又鼓的屍體就在宋仙河裏被撈起來——有人的,也有家畜的——但也有不少沒撈上來的,可能就爛在水裏被魚蝦啃了。
原本的宋仙河水是澄澈透亮的。划船行駛在水面,能看清河裏的魚蝦,真就像古人說的“皆若空遊無所依”。而山洪過後的宋仙河,不僅水質開始發渾,而且從老遠就能聞到一股腥味。
老頭抽着煙,緩緩地將過去發生的事娓娓道來。
我問他,那你們每天都喝宋仙河裏的水,不嫌惡心嗎?
老頭說,因爲那場山洪,本地人早就不喝那裏的水了,我們每次都去很遠的地方打水,只有外地來的那些遊客不知道。
接着他話音一頓,又說,不過我們不喝那裏的水,還有一個原因。
他說,自從那場山洪褪去後,每年都會有人在宋仙河裏離奇溺斃。
一開始還沒人在意。然而隨着溺斃的人越來越多,一直演變到後來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家畜或者人的屍體在河裏被發現。那時人們才覺得事有蹊蹺。最後還是村長出面請了一位先生過來,那先生很厲害,上來就說這個地方以前淹死過不少人,是“它們”在抓交替,要想辦法送它們去投胎纔行。
聽到這,我不免有些脊背發涼。
老頭敲了敲煙桿,接着說道,當時村裏有個一直要不上孩子的女人,走夜路不小心跌進了宋仙河,嗆了好幾口水。幸虧她命大,有路過的把她救了上來,結果那女的回到家,沒多久就懷孕了,她生的孩子屬豬,太陽穴那裏有一處胎記……說着,老頭從襖裏摸出一張照片,照片上的男人太陽穴正好有一個胎記,老頭說,這個男人也屬豬。
我對着照片上的男人相面,突然覺得他眼熟。我甚至覺得,如果地生能平安健康地長大,一定會長成照片上這個男人的樣子。
老頭說,這個男人長得很像地生,對不對?
我說,對。
老頭說,這個男人姓王,早在2001年就死在那場山洪裏了,他活着的時候和地生毫無關係。
我說,什麼叫活着的時候毫無關係?
老頭說,我說的那個女人就是我的妹妹,她的孩子就是地生,地生就是當初死在山洪裏的王姓男人的轉世,只要有女人喝了宋仙河的水,就能幫水鬼們投胎。
他咯咯一笑,說:
“宋仙河,請河仙……
“你以爲請的真是河仙?
“那送的都是水鬼!”
8.
老頭說,村子裏的人都對這件事守口如瓶,瞞着那些前來求子的夫妻,把宋仙河宣傳成了求子聖地,這樣一來,發生在村裏的怪事也果真少了。
但是久而久之,這件事也開始逐漸變質,現在但凡宋村有人去世,骨灰便會被家屬撒進宋仙河,以此幫助他們順利投胎。
我想起求子儀式上的那幾個空了的木盒,還有那些看起來異常喜悅的村民,頓時心生寒意。
我說,可是爲什麼那天我還是會被東西給纏上呢。
老頭說,可能湊巧了,一般這種都是等不及了的,就想抓你去做交替,它好去投胎,地生應該是替你擋了一災。
說着,他嘆了口氣,說地生最後還是把命給還回去了,其實也怨不得你。
於是我們和老頭告了別,連夜趕路回家。我坐在後座,昏沉沉地望着宋仙河。
那團白霧又出現了,影子們依舊在河中央漫無目的地遊蕩,而這次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
回到家後,我將這幾天發生的一切在心裏反覆咀嚼。打開家裏塵封已久的兒童房,那個穿着蓬蓬裙的身影一頭撞進我懷裏,頭頂的兩顆小櫻桃一晃一晃。我緊緊地抱着她。
她問,媽媽,你去哪裏了,怎麼纔回來呀。我說,媽媽出去旅遊了。她說,媽媽,你怎麼都不想我。我眼淚一下子掉出來,抱着她不停地說,媽媽好想你,妞妞,媽媽一直特別想你。
她撅着小嘴,說,那你怎麼都不想找我。
我抱着她,不停地說着對不起。我感受到她的小手是溫熱的,她的小身體是溫暖的,我貼近她左邊的胸腔,咚、咚、咚……我聽見心跳,像一個個不斷起伏的小山丘。
我摟着她,坐在她的公主牀上給她講《豌豆公主》,我看着她紅撲撲的小臉蛋,睫毛忽閃忽閃。我緊緊地抱着她,陪着她沉沉睡去。
被丈夫叫醒的時候,我懷裏的骨灰盒已經被我的體溫捂熱了。
我們又一次大吵一架。
或許是日復一日地照顧我這個瘋女人太累,他到底還是離開了我。從民政局出來的當天,他最後一次擁抱了我,讓我保重,然後頭也不回地上了一輛計程車。
而我在當天下午,獨自一人再次回到了宋仙河。我停下車,抱着骨灰盒去了河邊。
或許你們誰都不會理解,那是一位母親最後的、也是孤注一擲的希望與執念。
而如今,我已經懷孕六個月有餘。我摸摸自己鼓起來的小腹,感受到那裏真的有一隻小手在隔着肚皮撫摸我。
妞妞,我的妞妞。
媽媽終於要再見到你了。
END-
作者|一青一見
歡迎關注我們,
你愛看的奇聞、熱點、懸疑、腦洞都在這裏。
喜歡的話不如點個贊支持我們鴨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