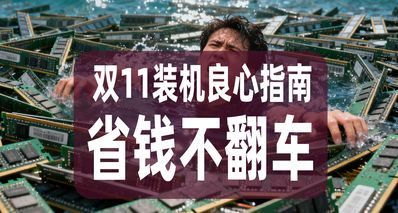文/文傑&二絃
導語
許多遊戲在立項的第二天就死了,但很久之後才埋。
成功往往相似,失敗卻各有不同。
一款遊戲的成功需要滿足一系列必要條件,外加一點運氣,但只要踩中一個坑就可能會萬劫不復。我們曾目睹過許多外表光鮮的遊戲死亡,也會爲一些頗有亮點、卻一不小心墜入深淵的項目扼腕嘆息。
一位製作人曾跟我描述過項目推進時的如履薄冰,一定規模以上的遊戲製作是一個複雜工程,前路上永遠會有預期外的坑。
雖說大多數人很難真正從別人的經歷中汲取教訓,只有自己踩坑才能從真實的體感中得到積累。但多看看別人經歷過的失敗,或多或少還是能夠有些警示作用。
本期遊茶圓桌,我們與行業者們聊了聊:“一個項目會因爲什麼而死掉?”
▍漕河涇流浪者 大西王
我所經歷的項目死掉,總結下來就一個原因:閉門造車。
從老闆到製作人,再到中層管理全部洋溢着奇怪的自大,拒絕一切外部經驗,迴避一切意見建議,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做,驗證是不需要的,反饋是不重要的,只要開發完成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項目開發過程中也有組織過一些小規模的玩家體驗與訪談,但玩家的反饋問卷只是走個形式,訪談會更有製作人一個一個親自回懟,之後又轉頭投入進開發小天地中,不知玩家市場爲何物。
如此這般閉門造車總不能永遠持續下去,當玩家測試規模越來越大,數據爛到再也無法假裝看不到的時候,自大就會轉變爲恐慌,慌不擇路的瘋狂調整項目方向試圖自救,最終因爲積重難返、數據稀爛徹底入土。
▍昨天離開遊戲行業的 Miguel
其實獨遊項目,死掉的過程挺普通的。就像慢慢溺水,每個問題看起來都能憋氣熬過去,但最後所有問題都會一起壓上來。
我自認爲根本原因,還是我們自己創意和現實脫節了。幾次測試,玩家的反響都不好,那時候太固執,總覺得玩家沒耐心體會,捨不得推翻重來。
然後就是那個惡性循環:接外包賺生活費 → 項目停滯 → 錢花完了接更多外包。有時候,我們做外包做得,甚至都不碰自己的項目。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是在假裝看不見吧。
我有一天改效果到凌晨三點,突然意識到我們不是在前進,只是在原地修補。這時候承認項目已經死了,反而比硬撐着更輕鬆。
▍退役3A老兵 XX
絕大部分的遊戲在立項的第二天就死了,但是一年半載甚至更長時間之後才埋。
▍想要穩中求勝的磁帶
不可否認,絕大部分買斷制遊戲生命週期較短,在上架後的一個月或者更短的週期內就能預測到項目的ROI,也就意味着買斷制遊戲對後續的運營投入通常會比GaaS少很多。因此買斷制遊戲項目的死一般指在開發階段胎死腹中。
以發行商或者投資商的角度來說就是對項目停止投資,對開發團隊停止“輸血”,那麼有哪些原因會讓信心徹底喪失,導致項目的死亡呢?
我的經驗僅限於在於獨立遊戲項目上,選擇合作以及對項目投資是一場多維度的風險評估:一個可玩並有潛力的demo、清晰的市場定位與獨特性、未來開發的規劃與想法、一個“看上去”靠譜的團隊。
評估遊戲項目未來潛力是合作的前提,除此之外我認爲最難以預見的就是團隊的穩定性,獨立遊戲開發通常是個人或者小型工作室,核心成員很少有成功的項目經驗,或者成熟過硬的技術實力。在接觸期我們僅能有限的瞭解到他們的溝通協作能力,清晰的項目計劃,以及是否擁有“有紀律的熱情”,這是遠遠不夠的。
人力角度:核心人才的流失與團隊的擴招;人力規模與項目野心的平衡;技術或人力不足導致的開發效率問題。
項目把控角度:不斷添加新想法新功能,項目邊界擴大,導致無法完工,甚至偏離了最初的核心玩法;由於團隊能力的欠缺導致的技術債務堆積,bug頻出導致的開發效率指數級下降。
都說一個“無聊”但完整的遊戲,比一個“有趣”的半成品更糟糕,因爲前者至少能賣。
但即便經歷了遊戲創意的取捨、開發週期的延長等問題,項目最終落地了,我們還要面臨最後一道砍兒,也就是遊戲市場風向的變化,“比如此時還在流行動作肉鴿,彼時熱度就被3A動作擠壓的一點不剩”。因此在出現項目危機時,投資方往往會通過項目健康度評估來決定是否繼續保持合作還是及時止損,也就是一個買斷制遊戲項目的存亡。
由於類似以上的種種原因,導致當下的獨立開發工作室必須把遊戲開發到70%或以上,才能端上臺面考慮發行合作這檔子事,而且遊戲核心玩法創意的長版必須足夠突出,因此也就註定遊戲開發完成度的上限不會很高,也算是國內獨遊開發環境的惡性循環。
但我依舊持有樂觀的態度,一切問題時間都可以解決,我相信總會有更多的高手或是開發與發行互相成就的巧合,逐步打造出中國3i遊戲的市場。
▍某從業者 lll
在說產品爲什麼死掉之前,我們要先討論,產品爲什麼要出生?
每個產品的生命週期,其實從他面世那一刻就已經確定了,決定產品生命週期的基礎就是產品本身質量。
在研發運營過程中的,營銷、輿情、事件、優化等等因素,其實都只是產品本身的映射。本質上,90%產品的衰退原因都是和本身的質量密不可分。
我認爲,核心原因和每個公司內部立項的初衷有關。無論是成功的項目,還是失敗的項目。
我見過太多隻靠主策和製作人的“喜好”和“理想”出發,做到一半發覺自己的產品過於小衆或者不夠普適(或者商業化能力不足),然後開始遷就用戶而調整,最後做成了“四不像”。
太多團隊因爲上述原因做出一個擰巴的產品——一個不符合時代、不符合公司技術、不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其中有極少數基於過硬的品質和實力還是能成功,但大部分產品,其實都是失敗的。
所以,一個項目會因爲什麼而死掉,我認爲最關鍵的就是這個項目的出發點是什麼?出發點決定了項目生命和模樣。有些產品,用換一句很電視劇的話來講就是,“這個孩子就不應該出生”。
▍里程碑亡者 -D
一個項目會因爲無限制的加班衝刺而死掉(確信)——來自一個正在加班的苦逼策劃。
當然這句話是開玩笑的,加不加班、項目環境惡不惡劣,甚至盈利能力達不達預期……基本都算不上能決定項目會不會死掉的決定性因素。
真正會讓項目死掉的直接原因只有一個:老闆/投資人本身不想繼續了。隔壁項目上線一年,玩家持續流失,幾乎始終保持虧損運營,研發人員更是走了一批又一批,但只因老闆認爲這個品類必須有一款像樣的產品,所以項目一直堅挺地撐下來了——當然更多時候,老闆的決定帶來的是宣告項目解散的壞消息。
除了上線項目有明確的必死信號(營收不抵服務器成本)外,在研項目能否上線、能撐多久,往往是一個研發成員幾乎無法觀測的問題。可能前兩天還是風和日麗,大家福利拉滿,嘻嘻哈哈地團建放鬆,過了一個週末項目突然沒了。
也可能項目內部人心惶惶,排期目標永遠完不成,人人都覺得品質有問題要褒姒,但項目永遠有新的hc,永遠新的成本投入,上線似乎遙遙無期,但研發多年依舊屹立不倒。
從前一個業內的朋友說,加班不是爲了完成產出目標,而是爲了緩解老闆的焦慮。有時候這班加着加着也確實會迷茫:我們在漫長的研發期裏不停地“衝刺”,到底是爲了把項目做好做上線,又或者僅僅是爲了穩定老闆的情緒,讓項目不至於死在猶未可知的黎明之前?
▍前二遊製作人的項目死亡指南
從開會到預算,那些讓遊戲夭折的陷阱:
會議室裏的空談、過剩的預算、失去方向的團隊,正在悄無聲息地扼殺着一個個遊戲項目。“我們從來都是總結成功的心得,鮮有回顧失敗經驗,傷口上撒鹽麼。”一位從業者在總結項目失敗教訓時寫道。在遊戲行業光鮮亮麗的成功故事背後是更多項目默默無聞的失敗。這些失敗並非偶然,而是從開會、預算、勇氣到重點把握的系統性崩潰。
會議本應是解決問題的平臺,卻常常成爲項目死亡的第一現場。有效的會議需要完成三個關鍵動作:訂立明確目標、確定可行方法、確定具體執行路徑。許多項目負責人忽視了這一基本準則,沉迷於“爲講而講”的自我滿足。主策劃爲了講話而講話,團隊負責人帶領大家討論抽象問題——如遊戲是否需要劇情,甚至通過舉手投票解決專業問題。這種缺乏明確議程和決策機制的會議,直接導致團隊方向模糊、效率低下。當團隊成員對會議結論理解不一,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努力時,項目已經開始走向死亡。模糊的目標使團隊成員陷入重複勞動和方向偏差的泥潭,浪費寶貴的開發資源。
反直覺的是預算過多有時反而會加速項目的死亡。一個有100萬-300萬預算的小團隊,往往目標明確,負荷均衡,執行高效。但當預算膨脹到2000萬,團隊規模擴大後,卻常常出現“忙的忙死,閒的閒死”的資源分配失衡。這種失衡不僅導致效率下降,還會引發團隊矛盾。當資源分配不當時,關鍵任務可能因資源不足而延期,而非關鍵任務卻可能佔用過多資源。在混亂中,團隊溝通成本飆升,內部推諉扯皮取代了共同解決問題。
當項目測試數據不佳或商業化表現不如預期時,團隊最容易陷入兩個極端:要麼貿然放棄,要麼死磕到底。許多團隊缺乏深入核心問題的勇氣,寧願在表面修修補補,也不願直面項目的根本缺陷。成功的調整需要團隊有“脫胎換骨的勇氣”和“重新解構的耐心和細緻”。當遊戲無法達到預期時,團隊應當深入遊戲內部,理清所有框架、功能、關聯、數值和交互關係。
在修改過程中,常見的錯誤是試圖同時解決所有問題:“加功能”“補內容”“做優化”全都要。這種面面俱到的做法往往適得其反。修改的重點應該有明確優先級。首要任務是優化玩家的核心流程體驗和正反饋,把玩家留下來。然後纔是根據體驗開發功能、增加玩法。付費設計應該建立在良好的留存基礎上。
除了上述核心問題外,遊戲項目還有多種常見“死法”,比如技術缺陷是遊戲運營的“隱形殺手”,技術穩定性對於依賴實時互動的遊戲至關重要。盲目跟風與創新不足同樣致命。職權混亂、工作流程不合理以及團隊對項目缺乏認同感,也是項目死亡的常見原因。當團隊成員“自己都不願玩自己這一類的遊戲”時,項目已經喪失了靈魂。
遊戲絕不是策劃、程序與美術的機械混合物,而是一個需要自然人來完成的有機體。許多管理者認爲拍腦袋決策、閱讀行業大佬文章、聽取從業人員吹牛就能發現機會,然後按照策劃案“施工”即可完成遊戲開發。這種思維誤區等同於“看着菜譜就以爲自己是名廚,能夠烹飪大餐”。遊戲開發中的“少許”、“適量”“酌情”如何把握?火候如何掌控?這些都需要經驗與直覺。
最後這個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說,大部分公司決策者在我看來因信息過載而與真正創造價值的“戰場”(即遊戲本身)產生了嚴重的認知脫節。
決策者每天接觸海量的行業動態、市場數據、同行觀點和自媒體分析。這些信息本身是有價值的,但危險在於,它們極易構築一個抽象的、“理想化”的虛擬市場,並讓決策者沉迷於在這個抽象層面進行“戰略推演”。他們談論的是“二次元賽道”“Party Game趨勢”“買量模型”,卻忽略了所有這些宏觀概念最終必須通過一個具體的、好玩的遊戲產品來承載和實現。當決策的依據主要來源於外部分析報告和零星彙報,而非對自身產品血肉相連的深度體驗時,這種決策就如同在沙地上建樓。
“完整跑一下流程”,恰恰是戳破了這種認知泡沫的最有效方式。一個從未以普通玩家身份完成從下載、新手引導、核心循環到付費點體驗全流程的領導,根本無法理解玩家在哪個環節會因冗長的加載而煩躁,在哪個任務節點因設計不合理而卡關,又在哪個付費點前因價值感知不足而毅然離開。他們下達的修改指令,往往是基於“我覺得”“數據顯示”或“別人成功了”的抽象概念,而非“我玩到那裏時,也覺得很難受”的真實體感。這導致了執行團隊(他們深知產品細節)與決策層(他們活在宏觀信息裏)之間出現巨大的認知鴻溝,修改指令自然顯得隔靴搔癢甚至南轅北轍。
那有沒有應對之道呢,有的兄弟有的,那便是強行將決策者的注意力從“潑天的富貴”幻想和龐雜的信息海洋中,拉回到遊戲最本質的“第一性原理”上——它是否好玩? 這要求決策者必須成爲自己產品最苛刻、最忠實的玩家。不僅玩還要帶着團隊一起玩,組織“Bug Bash”(找茬大會),匿名收集一線員工(尤其是客服和社區運營)從用戶那裏聽到的最真實、最刺耳的反饋。決策的根基應從“行業報告說……”轉變爲“我昨晚玩到第三關時發現……”。
最後,大部分責任確實是製作人本身的,因爲這些問題都是之前我實際遇到的問題和發生在我身上過的。 我見過的國內製作人很少有玩自己遊戲的,大部分都是到版本期了裝模作樣玩一下隨手指點下江山。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