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做柳宗元。字子厚。
公元773年,也就是大曆八年,那一年我降生在京城長安。我的家族是聲名顯赫的河東柳氏,歷經數代顯貴,先輩曾有人官拜宰相,然而到了我出生的時候,家族氣勢已不如昔日鼎盛,所謂“世衰族微”便是如此吧。
儘管如此,我依然引以爲傲的是,我父親柳鎮秉性剛正,明經出身,曾經擔任過殿中侍御史,剛正不阿。我母親盧氏出自范陽盧氏,知書識禮,信佛向善。
到四歲的時候(公元777年)我還年幼,就跟着母親居住在長安西郊的莊園裏。那年春天,長安城外的田野之間仍然瀰漫着寒意,母親就帶着我坐在院子中,朗聲誦讀着詩文,母親在我耳邊輕聲說:“”此後啊,你當靜心讀書,日後做一個博學、有用的人。”我看着她溫柔卻堅定的眼神第一次感受到知識之光的溫暖。那個時候父親因爲公務經常不在身邊,所以母親就成了我最初的啓蒙老師。
公元782年,那年我九歲,這一年爆發了“建中之亂”,烽火驟起,朝廷和藩鎮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曾經繁華的長安城被戰火的陰霾籠罩,聽聞亂兵或許會攻破城門,母親帶着我一路顛簸,去了父親所任的夏口(今武漢一帶)投奔。
之後,到了公元785年,那個時候我12歲左右,戰火稍息,父親奉調赴江西任職,我又跟着他輾轉,父親爲官清廉,不懼權貴,常常直言進諫,卻也因此得罪了朝中的權臣。
有人勸父親稍作退讓,父親卻一臉堅毅:“吾目無涕”(我眼中無淚,即不屈服的意思)。他彷彿在說即使屈居人下也無懼強權,無愧於心。
我悄悄站在父親身邊,我那個時候雖然年少,卻對這鏗鏘之言銘刻於心,我心裏也常常想起那些受戰亂之苦的百姓,也愈發感到國家積弊之深。
也是那一年,番將李懷光叛亂被朝廷平定,南方州郡一片歡騰。崔中丞聽聞我讀書勤勉又略有文名,竟派人來請我代他寫一篇《賀平李懷光表》上奏皇帝,我雖惶恐,卻不敢懈怠,所以我仔細斟酌措辭,對仗要工整,詞章須典雅。忙碌幾日之後,我滿懷忐忑地呈上奏章,得到一片喝彩。大家都在傳頌那個名叫柳宗元的少年,他們說柳宗元是神童啊,所以寫完了一篇奏表之後,我終於發現了文字的力量,不僅能夠怡情養性,更能參與國家大事。
我記得那時我趴在窗前,透過紙窗的縫隙看着漫天的星辰,我就開始暗自思量:書中的道理,如果能夠施行天下,或許亂世就能太平啊。文人的犀利筆鋒不正是另一種刀劍嗎?
孩童時期的動盪與見聞在我胸中埋下了一粒種子,隨着所見所聞不斷生長,就這樣我懷着少年心氣在母親的授書,父親的教誨中一路成長,我目睹了朝局的離亂,也見識過社會的百態。母親的仁慈與父親的剛直在我心底交融,成就了我對儒學與佛理的並行觀照,也讓我在日後的道路上愈發堅定。隨着歲月的推移,我心中逐漸凝聚出一個抱負,如果有朝一日能夠立足廟堂之上,一定要將筆墨化作利劍,匡正時弊,拯救黎民於水火,這纔不枉讀書人的一片赤誠。
記得那是公元793年那一年我21歲,我站在長安的街頭心中那是澎湃不已,因爲我剛剛成就了少年的夢想——進士及第。然而這種剛剛步入仕途,準備迎接新挑戰的激動和驚喜,卻被一個突如其來的噩耗擊潰:父親去世了。
我急急趕回家中守孝三年,痛失親人的感覺就像冰冷的長安冬夜久久揮之不去。
父親過世的這三年讓我對命運有了更深的認識,但我知道無論如何生活還得繼續,悲痛逐漸化作力量,我重新出發,回到仕途。
公元798年那年我26歲,我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順利通過,這一次成功沒有讓我沾沾自喜,通過考試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與年少時不同的沉重。我已不再是那個只想着文學才子夢的青年,更多的是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

這一年我得以擔任集賢殿書院的正字,負責校對經籍,管理皇家圖書。雖然這個官職不高,但是也肩負着一份不可忽視的責任。我想起了我父親曾經告訴我,讀書不僅僅是爲了個人的光輝,更是爲了國家的興盛。我想或許就是這一句話,纔是真正驅動我繼續前行的力量吧。
歲月匆匆,公元801年,那年我28歲,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被任命爲藍田尉,重新回到了基層當中。
我開始接觸到更多的社會現實,生活變得愈發複雜,不再是單純的書齋與紙上談兵。我那段時間見到了無數貧苦百姓的疾苦,開始投入更多的心思在政治改革上,我逐漸明白好像:文字的力量遠不及實際的行動。我想我心中的理想與抱負注入每一份報告,每一篇奏章中,特別期待能夠通過這一條路改良百姓的疾苦,重建國家的秩序。
公元803年那年我30歲左右,最令我難以忘懷的還是那段在監察御史任職的歲月。我與劉禹錫、韓愈兩位摯友共同在這一崗位時,我就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同事,更像是知己跟夥伴。我們每天討論的不僅僅是文學藝術,更多的是國家的改革還有未來。我們都盼望着能以一腔熱血爲這個國家帶來新的氣象。
是的。我知道,我們想做的這個事情叫做“改革”。我也知道看了那麼多史書,所有的改革之路都充滿了荊棘,但我已不再是那個單純的文學青年,我已經意識到所謂文學才子不僅僅是在文辭上求得一時的盛名,更是要通過實際的行動來承擔國家的重任。但我從來沒有想過理想與現實之間會有一道深不可測的鴻溝。
曾幾何時我跟王叔文、王伾、劉豫錫等人一道,懷揣着救國安民的雄心壯志推行改革,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讓大唐恢復昔日的盛世輝煌,所以我們全心全意推行了被後世稱之爲“永貞革新”的改革。這個革新有很多方面:從打擊藩鎮、整頓稅收到廢除宮市、懲治貪官,改革舉措就像春風拂面,那個時候真的振奮了無數民衆的心,但是“永貞革新”沒有進行多久,命運的脈絡遠比我們所願意看到的更加複雜。
公元805年,那個時候我32歲,正值壯年,我也站在權力的巔峯,我因爲跟王叔文等人的政見契合得到提拔爲禮部員外郎,掌管着整個國家的禮儀、祭祀與貢舉。我們推行的“永貞革新”受到了宦官、藩鎮以及許多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雖然短期之內民衆的支持給我們帶來過一絲希望,但是權力的博弈始終充滿了不可控的變數。曾經支持我們的順宗帝病情加重,已經無法繼續理政。而宦官集團的那些太監們他們在背後操控着一切,宮中被他們攪得一片混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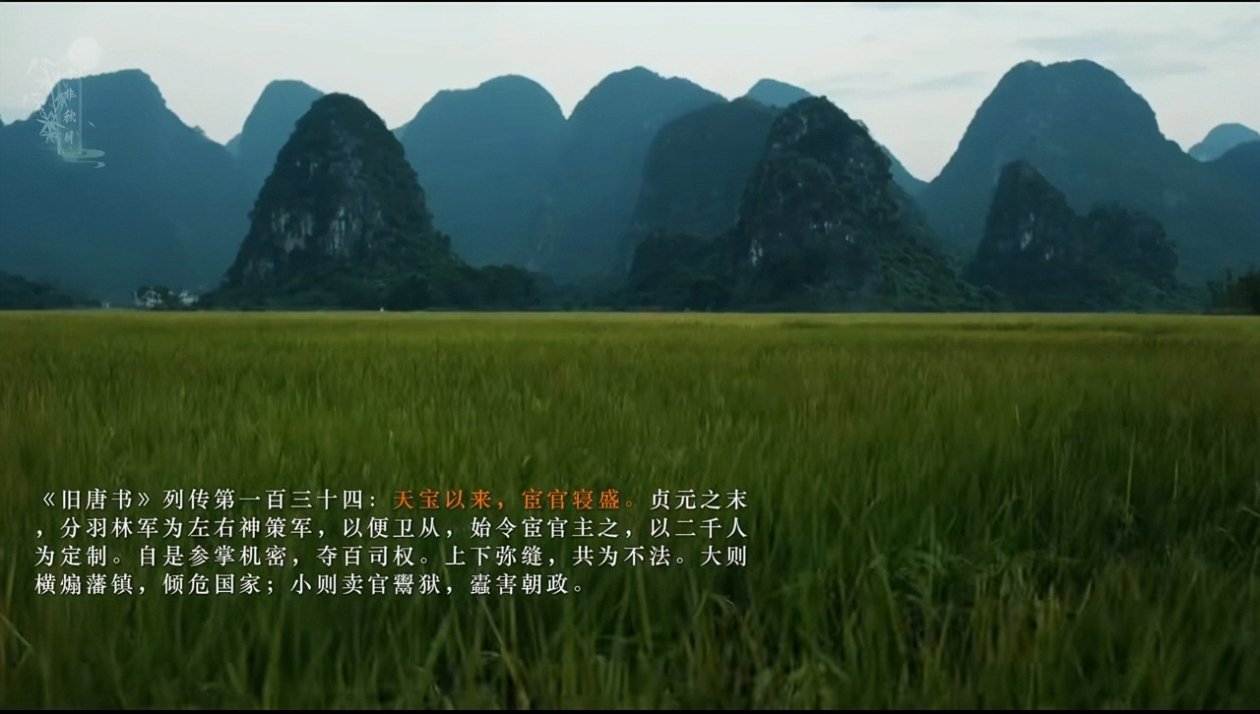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四月的一天,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歷史稱之爲“永貞內禪”。
李純繼位之後對我們革新派充滿敵意,在那個令人窒息的8月裏,我跟劉禹錫、韓泰、陳諫等人一同被貶爲遠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二王八司馬”。
唉,改革的夢想在無數的壓迫與爭鬥之中,破碎了,最令我感到心寒的不是外界的打壓,而是許多人開始跟我還有我的那些同僚們,跟他們劃清界限,我那個時候都要崩潰了,我背後是曾經的同盟與朋友,而眼前是劃清界限的敵人,還有權力的無情,我心中只有無法言喻的惆悵,還有無奈。
我看着那些背棄的眼神我心中湧起一股憤慨我說爲什麼要在權力面前低頭?爲什麼要放棄我們曾經的理想與奮鬥?
我又開始回想起父親曾經面對困境時說過的那句話:“吾目無涕”。是,正是這一句話讓我在逆境當中仍能保持一顆堅韌的心,始終不向命運屈服。
公元806年八月,那一日我接到憲宗的詔令心中像是被重重地擊打了一下,聖上說“”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意味着以後哪怕聖上大赦天下,你們這些人也不在我們考慮的範圍之內。特別絕望,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只能帶着母親,還有僅存的那一份親情踏上了這一條命運交錯的漫漫貶途,我被貶的地方叫做永州(今湖南永州),
永州遠離京城,幾乎與世隔絕,這裏的環境惡劣,氣候溼熱,滿地蛇蟲野獸,讓作爲北方人的我更是水土不服,而更加讓我難以忍受的是母親的病痛,在那個地方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醫療條件。公元807年五月,她就在這裏因病去世,
我就想起母親隨我四處遷徙,忍受風雨辛酸。我想如果我柳宗元沒有被貶,那這個溫暖的家本該繼續在長安,我定會讓她得到最好的照料,安享晚年,而如今她卻未能熬過這荒涼的歲月。
母親去世之後的幾年痛苦如影隨形。4年後我的女兒也在永州病逝,看着她年幼的面龐漸漸消逝,我幾乎失去了所有的力量。
一個接着一個的打擊就像海浪一樣把我拍到了無盡的深淵裏。我那段時間曾經想着嘗試:我要振作,我想用文字跟理想填補內心的空虛和悲傷,但每一次動筆淚水都會模糊了我的視線,這種身體上的痛苦與心靈的折磨交織在一起,令我幾乎無法忍受。
你說我柳宗元啊,我柳宗元曾幾何時站在朝廷的中心,懷揣着改革的理想,我盼望着爲大唐復興貢獻一己之力。而如今我只能在這一片遙遠的荒土中回憶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夢想,任憑時光無情地摧殘吧。
在永州的日子裏,我不僅要忍受自然的惡劣環境,還要跟無盡的痛苦與內疚作鬥爭。我的性格本來就不外露,所以痛苦就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我的身體也漸漸的衰弱,我的牙齒不知道爲什麼開始鬆動了,雙鬢也開始變白了。我那個時候只有30多歲,臉顯得老態龍鍾,形容憔悴,但即便如此,我仍然不曾後悔過自己的選擇。
在這荒涼的山水之間,在這一段孤獨的歲月裏,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漸漸地,政治的幻滅讓我從追求功名的理想執着轉向了內心更爲深沉的思考。我不斷地在寫作當中尋找自己,沒有豪言壯語,也不再渴望用文字去改變世界,我只是單純地記錄眼前的一切,每一次拿起筆,我都好像是跟過往的自己告別,又像是與未來的自己對話。
在這裏我與外界斷絕了聯繫,但是我內心的波瀾從來沒有停止,那些曾經的理想和抱負似乎並沒有完全消散,他們在我的文字裏找到了新的歸宿,所以我開始走出廟宇,走入山林,隨心而行,去體味這片大地的風光。我開始以一種新的形式與大自然對話,傾聽他們的聲音,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下了這篇小石潭記:“”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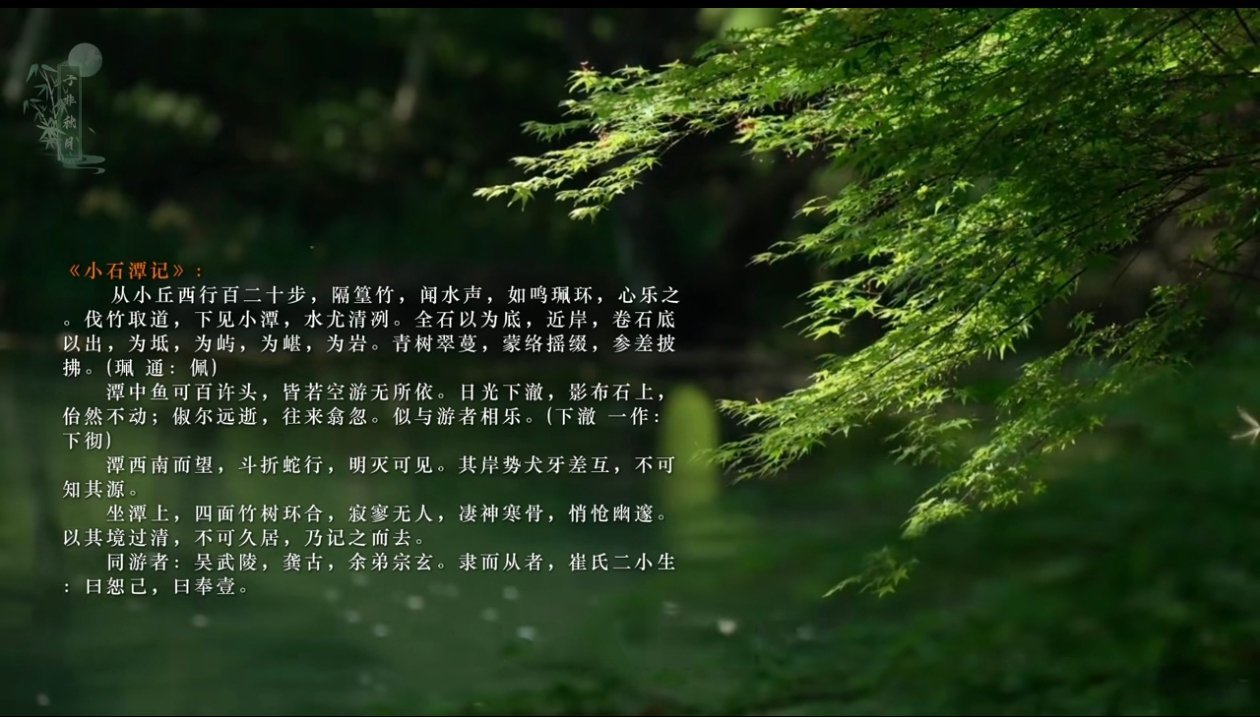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
這篇小遊記表面上看只是描繪自然景色,但是仔細品味裏面的情感和那一份深沉的寂寞,我覺得纔是最動人的部分。
誰能看到我筆下描寫的並不是大山大水的豪邁,而是一顆在孤獨當中逐漸明澈的心。
我的生命曾經因爲朝堂的風雲而波瀾壯闊,然而現在它已經悄然收斂,沉靜如潭,這不僅僅是一片山水的寫照,更是我柳宗元內心的真實寫照。
孤獨是我跟這個世界對話的唯一方式。
在永州的這些年,我慢慢學會了如何在孤獨與沉寂當中找到自己的安慰,我帶着我曾經的痛苦跟孤獨寫下了那一首《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其實這幾句詩就是我內心真實的寫照。我獨自乘船行於江上,江面泛着淡淡的雪光,四周一片蒼茫。在漫天飛雪當中萬物寂滅,一舟孤影就在江面上,白茫茫一片天地空無一物,世界好像停滯了,就像我的人生也停滯了。
是的。這雪地當中這江面之上,孤獨跟無助是我唯一可以依賴的伴侶,而我也在這無聲的雪夜當中釣取着屬於我的那一片寧靜。
元和十年,也是公元815年,朝廷傳來詔令,唐憲宗終於收回了他當初對“永貞革新”的決心,召我還有劉禹錫等人回朝。
我本來沒有太多奢望,我只希望能夠回到那個曾經承載我無數記憶的地方——長安:這裏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承載着我少年時的理想跟憧憬,我已經不再年輕了,我也不再對政治有着當年的熱情,但是總能找到一絲慰藉吧,哪怕只是返回故土。我記得自己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滿懷着夢想滿是熱血,但是我心中的那一份激情,在這10年永州歲月中早被磨掉了。
十年飲冰,心早已冷卻,故鄉啊。即使我知道我這一次回來或許再也無法恢復曾經的光輝,但回家了呀。
那就夠了。
拿到這份詔書,我忍不住淚如雨下,所以我那個時候興奮地寫下了《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我寫: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裏外北歸人。
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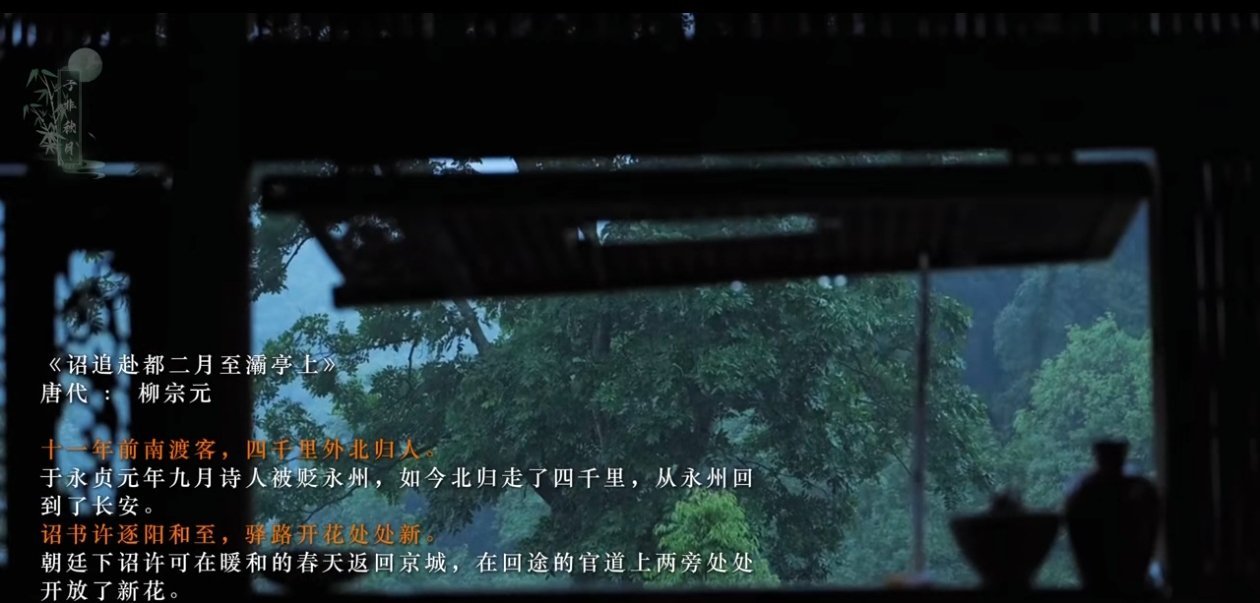
所以我回到了長安。
但是好景不長,我在長安的日子不過短短一個月,因爲劉禹錫寫的一首桃花詩再次遭到了政敵的陷害。劉禹錫寫的啥呢?他寫: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他說我劉禹錫又回來了,就是因爲這首詩,我們被政敵誣告“無悔過之心”再遭貶放。
我回來沒一個月再度被貶,我真是心如死灰啊,就像荒蕪大地上被隨風打翻的塵土,這一次我被貶到了柳州,雖然官是升了,但是柳州這個地方更偏、更遠。
我那個時候就知道:誒,遠離了長安,就是遠離了曾經的自己,但我其實不孤單,在這一片寂靜的土地上仍然有很多溫暖,比如劉禹錫,我的這位摯友因爲那首詩也被貶了,
但他身處的播州(今貴州遵義)比我被貶到柳州更爲遙遠艱苦,我心中特別不是滋味,我憂慮他老母(身體)的康健,所以我上書朝廷,我請求讓我們二人對調,讓劉禹錫到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地方,雖然朝廷沒有完全答應,但是將劉禹錫改調到連州(今廣東清遠),也算是我的一番努力吧。

但不管怎麼樣,我跟劉禹錫終究還是要分別。我們在衡陽分別的時候,我心裏特別不是滋味,誒,淚水在眼中打轉,曾經的夢想跟那些共同度過的時光都像流星一樣,我也老了,所以我那個時候寫下了《重別夢得》: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日歧路忽西東。
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鄰舍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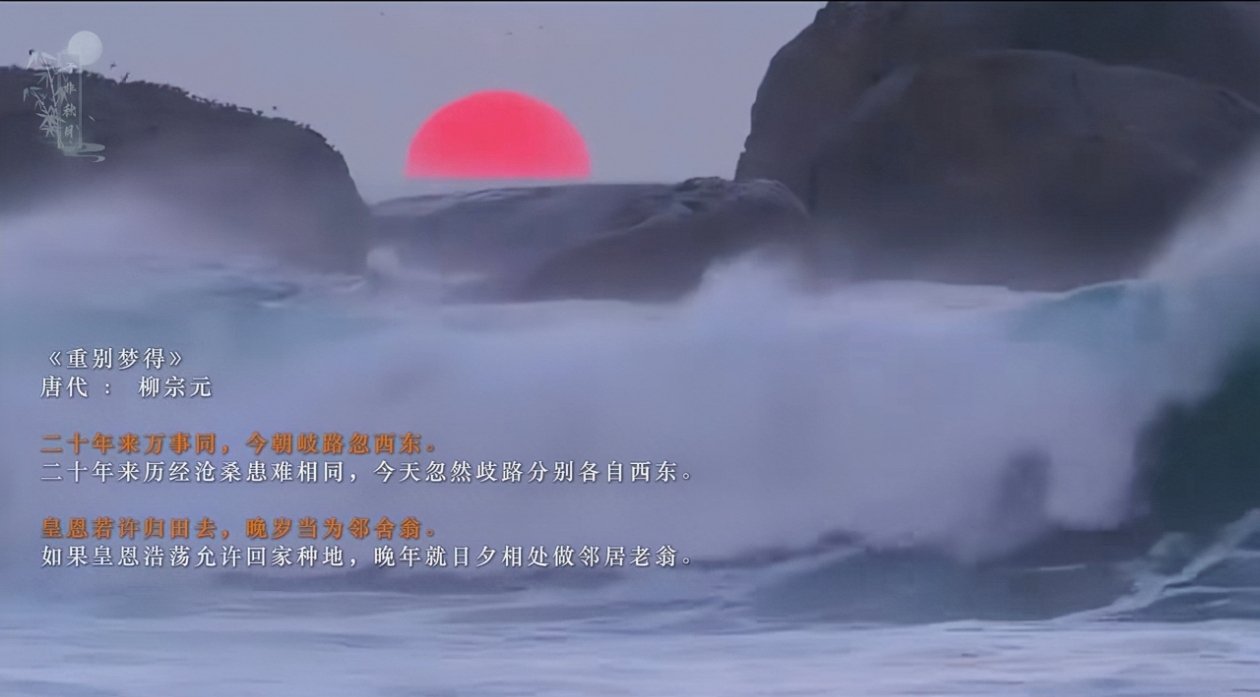
我們曾經一同走過那麼多風雨,陪伴彼此度過艱難的歲月。我多麼希望能夠在晚年的時候安靜地跟劉禹錫一起,過一過平凡日子,做兩個鄰里的老翁啊,但是這個小小的願望終究未能實現。
我們這一次告別,就成了最後的訣別。
我初到柳州身爲刺史,登上城樓遠眺四周,心中百感交集。
茫茫的沙野蒼涼、空曠。
我不禁想起與我一同被貶的劉禹錫還有其他志同道合的好友。曾經我們想着改變世界,但是現在天南地北,音信難尋,特別孤寂、傷感。
你說何時再能見面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到了柳州,我就揮筆寫下了這首《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用來寄託心中的無盡愁思: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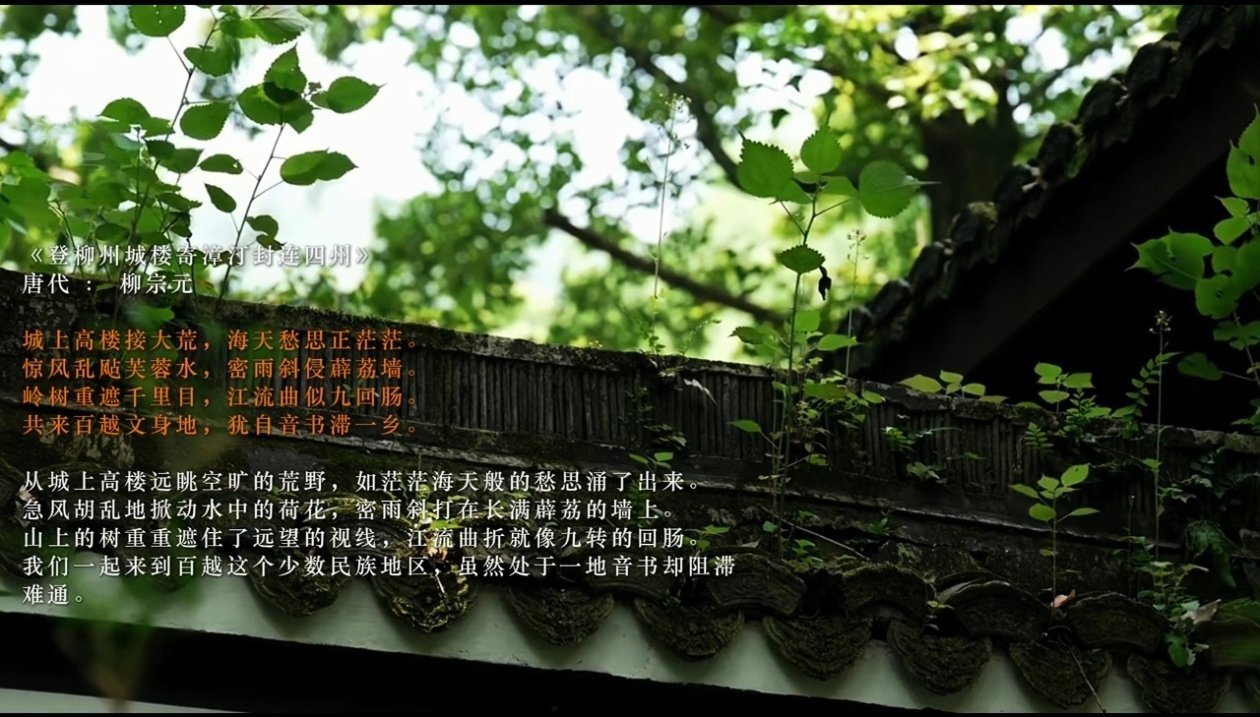
早在“永貞革新”之前我便有言:“致大康於民”、“心乎生民而已”、“無忘生人之患”,這不僅僅是我的政治主張,更是我立身爲官的根本理念。
所以我到柳州我就開始着手實行了許多改善百姓生活的措施。
首先我廢除了奴隸,解放了奴婢。在我們唐朝等級森嚴,奴婢我覺得就是社會的一大污點。他們地位低賤,就像是主人的玩物,直至生死都掌控在他們主人的手裏,而且奴婢的身份是世代相傳的。柳州作爲遠離朝廷的偏遠地方,我那個時候發現奴婢的制度尤爲嚴重,那些擁有奴婢的豪強地主對百姓的壓迫更是殘酷無情。所以面對這一種不公,我絲毫不畏懼權貴,我毅然決然地決定,要廢除奴婢的終身制,允許他們通過贖身或者勞動來獲得自由。
我希望通過這樣的改革打破奴婢的身份固化,我也希望爲那些無辜的百姓帶來一線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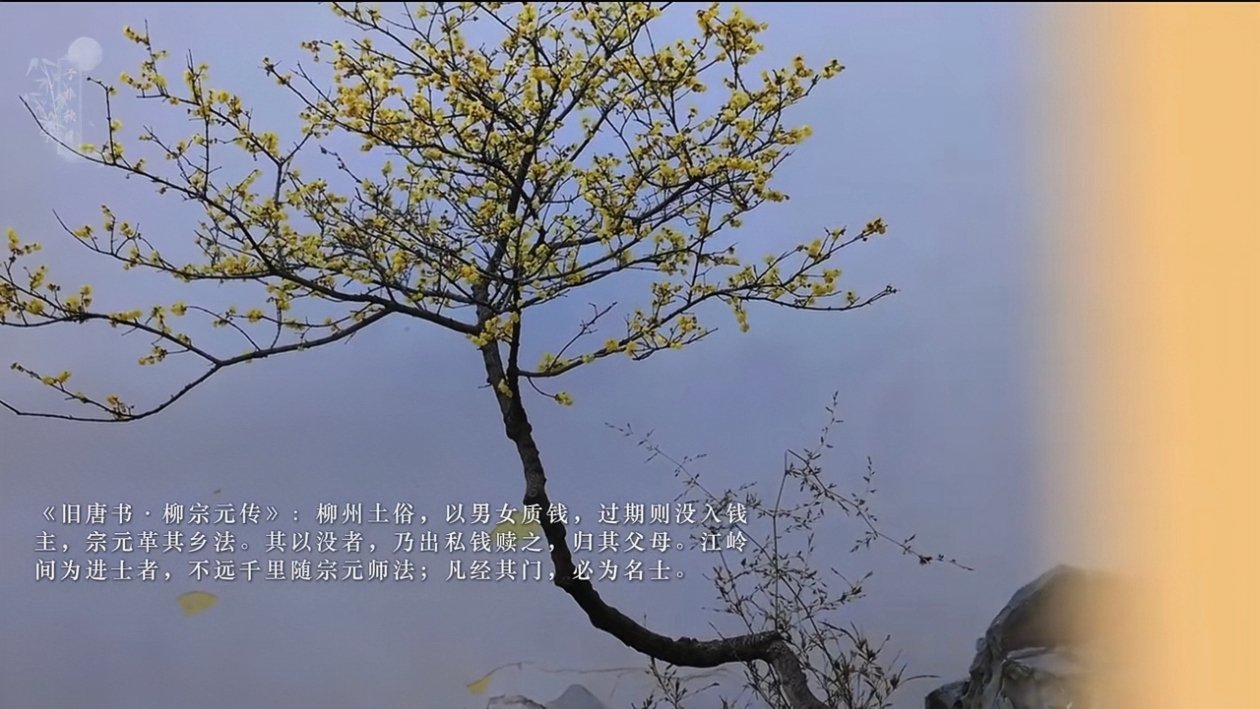
其次我又想到了民生,開始發展生產,柳州的地理條件雖然不如長安等大城市,但是我依然通過種植柑橘、竹子、柳樹等方式,極大地改善了當地的環境,爲百姓提供了更好的生計。我發現當地的居民想要打井(喫水)需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所以我就組織人口在當地打井,解決了人們的水源問題。
很多人都說我柳宗元做的是小事,但我覺得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實則爲百姓的生活帶來了實實在在的改善。
此外,我興辦學校,恢復了“府學”,提倡文化教育,來傳播中原的文化。當地的百姓特別迷信一件事情就是用雞來算命,他們還有獻祭畜生的陋習,我就利用我手中的權力強力破除掉這些迷信,推廣醫學,倡導科學。我知道只有通過教育才能夠真正地改變人的思想,才能爲國家的未來鋪路。在柳州的4年當中,作爲一名地方官員,我沒有低頭依附權貴,哪怕這樣可以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我也沒有迎合上級。我做的始終是以百姓爲本,精於州務,勤政爲民。
我堅信民本思想纔是治國的根本,唯有站在人民的這一邊,才能真正爲國家的未來打下基礎。就像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叫做捕蛇者說,那裏面寫“苛政猛於虎”,那些壓迫百姓的政令實則比猛虎還要可怕。我在柳州的所作所爲正是讓那些苛政遠離人民,讓百姓的生活得到實實在在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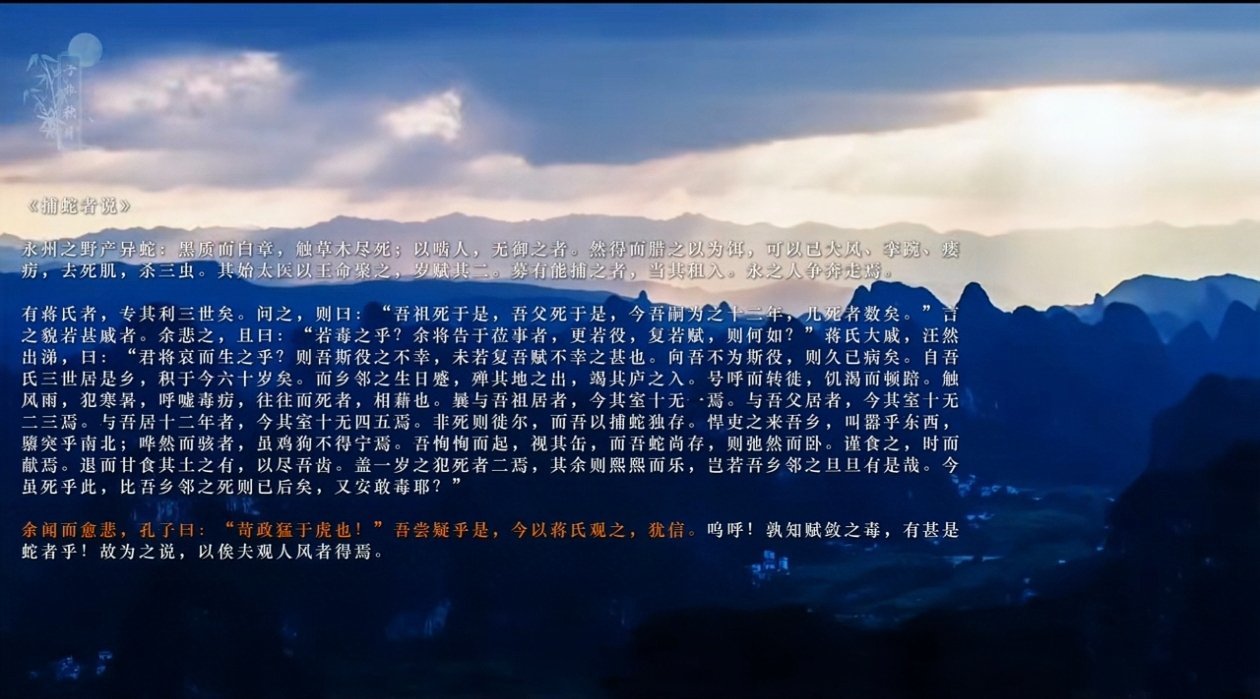
但是自從來到柳州,我的健康日益消退,我的身體幾乎被病痛吞噬,百病纏身。每一天的痛苦都拉扯着我的靈魂,但即便如此,我依然沒有停止爲百姓操勞的腳步。
雖然身體越來越虛弱,但我始終覺得“許國不爲身謀”,我寧願承受着這些痛苦,我默默忍受所有委屈我也不願意讓百姓的希望,因爲我,而破滅。正因如此,我拖着病體仍然堅守政務,我始終沒有放棄爲柳州百姓做實事的責任。
當時在長安的唐憲宗始終對我們這些人發起的“永貞革新”中的“罪臣”耿耿於懷,而反對派的攻訐與不斷阻撓,致使我重回長安的希望遙不可及,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我的心情愈發沉重,也正如我的身體越來越虛弱。
歲月無情,官場的失意與流亡生涯的孤獨就像,一股無法掙脫的陰霾時刻籠罩在我的心頭,我能做的就是爲百姓辦點事,而如今我好像也辦不了多久了。
那時,陽春2月的景象竟然像秋天一樣寒冷、蕭瑟。百花盛開,本來應該是生氣盎然的季節對吧?但是你知道那天突如其來下了一場暴雨嗎?
榕葉滿庭,溼漉漉的泥水四濺,黃鶯就在庭院中哭泣,這樣的景象讓我更加憂慮孤獨,所以我提筆寫下那首:《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
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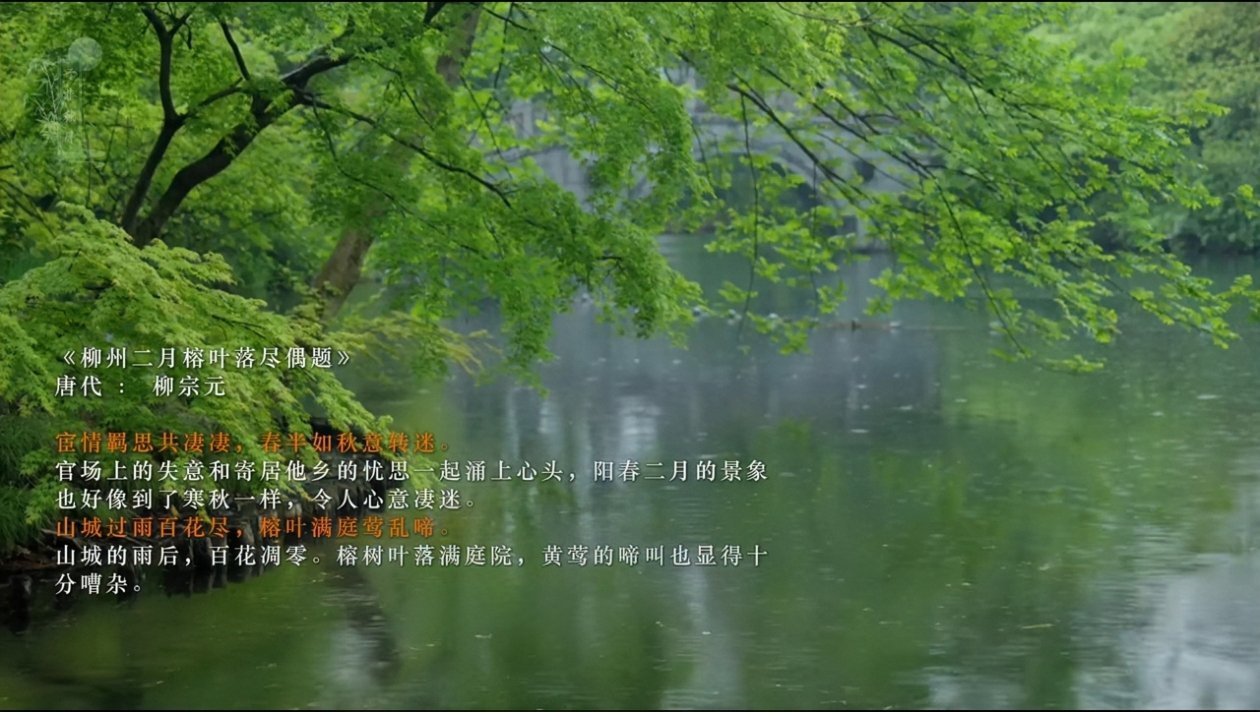
病痛,失意,鄉愁,這一切就像無形的枷鎖,讓我緊緊地束縛在那裏。
回望往事我不再年輕,頭髮早已花白。
歲月無情,我何時才能回到故鄉?
何時才能結束這漫長的“流亡”生涯?
我也不知道。
我的生命之沙正在悄悄流逝,我深知自己時日無多,所以那段時間我又開始寫詩:
“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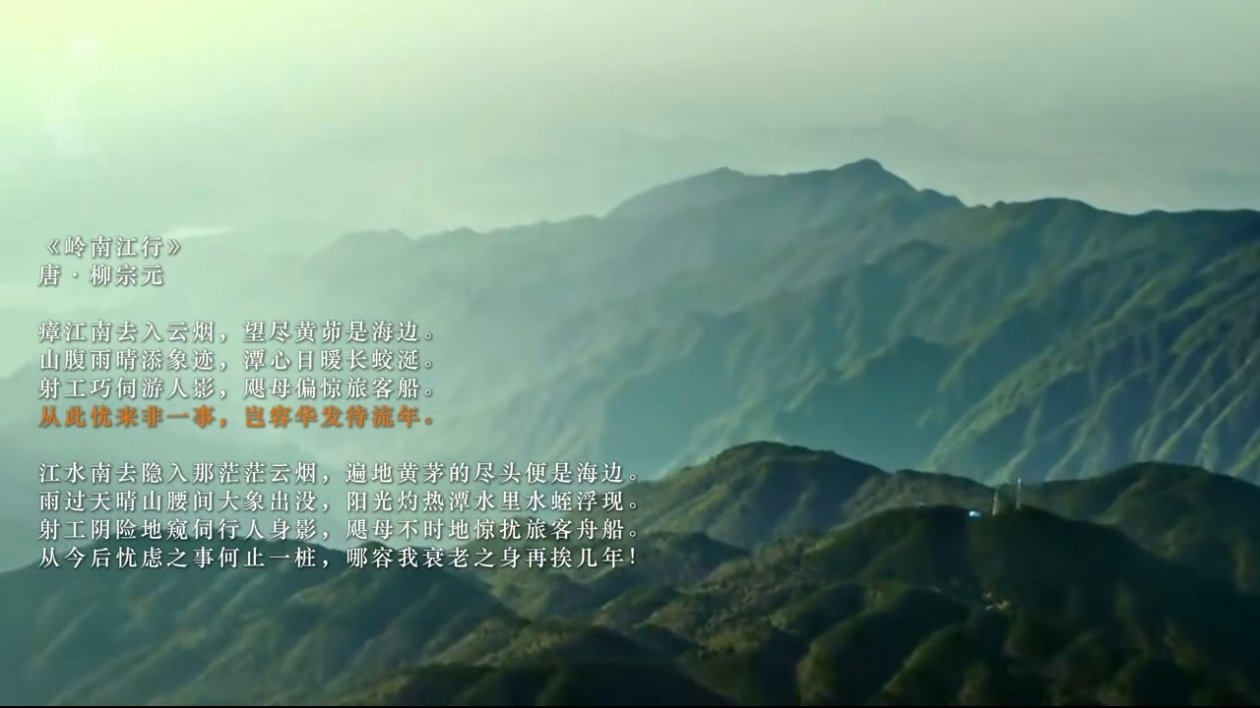
病痛折磨,政治失意,讓我的愁緒更加濃重。心煩意亂。
我因爲強撐着病體處理政務,我的身體也愈發虛弱,但,那段時間我的思緒卻經常飄向故鄉,彷彿那一座遙遠的山川仍然能給我力量。
所以我在詩中寫:
“海畔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歌愁腸。
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在我生命的盡頭我有一種深刻的預感,我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了,所以我開始料理我的後事。我把自己所有的作品整理好寄給劉豫錫,希望他能夠幫我把這些作品彙集成集。
我還有4個未成年的孩子,我把他們託付給了劉禹錫跟韓愈,我希望在我死後他們能照顧好這些孤苦無依的孩子。
與此同時,在長安,吳武陵、裴度等老友仍然在四處奔走爲我說情,他們力求把我調回長安,但命運就像我的生命一樣,早已經不在我的掌控了,還沒有能夠等到我回到長安,我就在柳州病逝了,年僅47歲。
是的。
我的故事,嗯,到這裏就結束了。
他的名字,叫做柳宗元。他是唐代文學的重要人物,不僅是古文運動的傑出代表,還是一位哲學家、政治家、詩人和散文家,他的作品涉及哲學、政治、文學等多個領域,影響深遠,至今仍然被傳頌。
柳宗元的哲學思想,繼承併發揚了唯物主義,批判天命論。他強調社會歷史是自然發展的過程,他在《天說》《天對》等哲學論文當中提出了“人”而非“神”的重要性,展現出當時對社會政治的深刻思考。
在佛學方面,柳宗元雖不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從佛教中吸取思想,將佛學與儒家思想結合,以達心靈的解脫,他的思想兼容幷蓄,成爲唐代思想的獨特風景。
柳宗元的詩歌語言樸實,風格淡雅,特別是在《江雪》、《漁翁》、《溪居》等作品當中,他通過清新俊爽的筆觸表達了流放期間的幽怨與哲理。他的詩歌展現了深沉的情感與思考,影響了許多後代詩人和文化學者。他的辭賦作品繼承了屈原的傳統,情感真摯,行事嚴謹。他的“九賦”和“十騷”代表了唐代辭賦的高峯,也體現出他在困厄當中的堅持與理想。在散文創作上,柳宗元和韓愈共同發起了古文運動,主張“文道合一”。他們提倡文章應該反映現實,批判時弊,而他的作品如《永貞革新論》、《捕蛇者說》等,不僅在藝術上有所創新,也在思想上引領了唐代散文的革新。
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永州八記》在中國古代山水遊記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通過細膩的筆觸和自然景色的描寫,表達了對自然的深刻感受和內心的抒發。除此之外,柳宗元的寓言作品如《黔之驢》、《遊某事之蜀》等,也通過生動的故事揭示了社會的不公與人性的弱點,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不可否認柳宗元的文學成就橫跨詩歌、散文、辭賦、寓言等多個領域,他的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均具有創新意義,並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無論是哲學思考還是文學形式上的突破,他都爲中國文化的傳承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他的名字,就叫柳宗元。
永州10年的冬月,他經常盯着結冰的硯臺發呆。長安的月光曾經照在翰林院的青磚上,如今卻碎在蠻荒之地的瘴江裏,但這個發呆的身影沒有放任自己溺死在憤怒中,他在潮溼的竹紙上寫《黔之驢》,筆鋒一轉竟成了預言大師。他給漁翁、樵夫、牧童立傳時,字字都沁着土地的生氣。
其實最讓我動容的就是他的矛盾。他寫《江雪》時明明在說:“天地間只剩我孤零零的一個人”,但他轉頭卻在柳州修水井、辦學堂、放奴婢,那個獨釣寒江的身影,懷裏其實揣着溫熱的人間煙火,就像他總說:“餘雖不合於俗”,可翻開《永州八記》,滿紙都是對一草一木的癡纏,
讀他的詩文,總覺得有雪粒子往骨頭縫裏鑽,不是蘇軾“大江東去”的曠達,也不是杜甫“沉鬱頓挫”的悲愴,而是像永州江畔那些嶙峋的怪石被命運反覆沖刷後,反而顯露出粗糲的生命力。
柳州城頭的木棉花年復一年的綻放,柳宗元最終也沒能返回長安,但他在精神荒野中開闢的道路,讓後世的文人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當廟堂之路斷絕時,思想的星空依然璀璨”,他的命運似乎就是從燦爛的榮光走向深沉的孤寂,但恰恰是在這樣的孤獨和落寞當中,他的筆觸開始變得更加有力,更加深邃。這種在絕境中的創造性轉化,讓中國文學史擁有了最蒼勁的冬日印象,也讓知識分子的精神圖譜上多了一條向死而生的曲線。他臨終前或許會回想起自己寫過的詩句:
“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風頭望故鄉。”
是的,那個昔日的長安少年最終沒能回到故鄉,卻在他用血淚澆灌的南方土地上長出了新的根系。這種在絕境中依然保持書寫姿勢的倔強,比任何華麗的修飾都更加接近文學的本質。這種本質其實更像是如今的我們竭力尋找的對抗異化的精神抗體。
你說當現代人困在996系統當中,被迫成爲“新永州司馬”時,那個在寒江邊獨釣的身影好像突然變得鮮活。他提醒我們:
“真正的覺醒,”
“往往始於承認所處世界的荒誕。”
“而人的高貴,”
“正在於,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後,”
“仍選擇在廢墟上種植一株思想的蘆葦吧。”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