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約6500字,前言部分(約2400字)無核心劇透,正文部分(約4100字)含劇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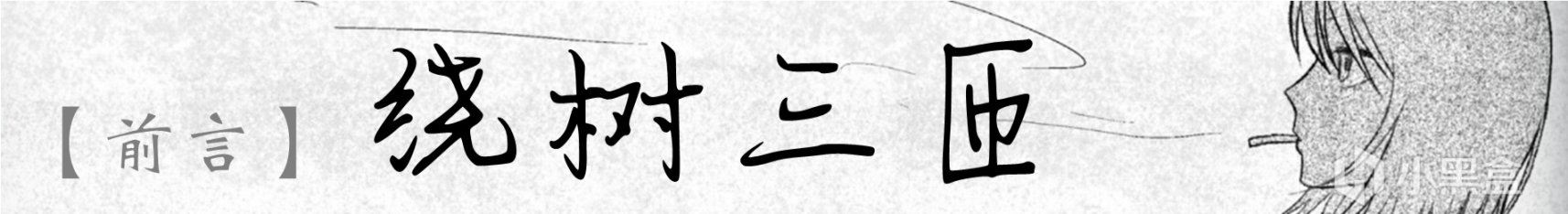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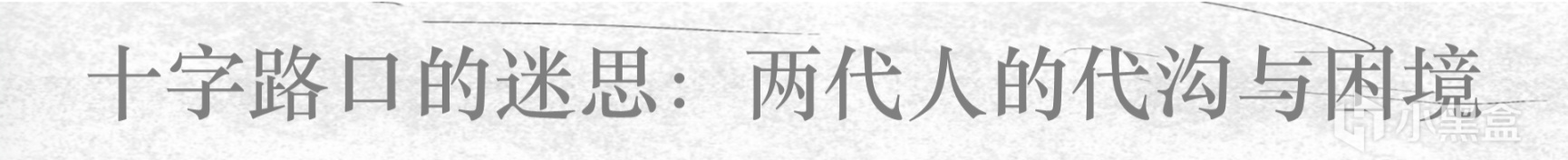
“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玩《紙房子》的時候,我想到了我的母親。
她的出生,本不在我外公外婆的意料之內,甚至基因的深層,都藏着打胎失敗的痕跡。
幸運的是,打胎並未成功阻止我母親的出生。不幸的是,她即將面臨的童年寫滿了困苦曲折。
藥物的作用讓她直到三歲才能說話,童年的傷害更成爲未來無數個夢境裏揮之不去的陰影。
《紙房子》中趙穎的出生,也是一場意外,她的處境就好像復現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只生不養的農村常態。只不過彼時的情形,源於物質匱乏年代的集體陣痛。而遊戲所展現的悲哀,來自重組家庭代際關係的僵化。
在這個重組家庭中,趙穎便是不受待見的那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趙子璇含着金湯匙長大,而趙穎,得到零星關懷已是空谷足音。

回望我母親的童年,境況大抵更爲糟糕。上有備受重視的大姐,下有惹人憐愛的小妹,還有哥哥——家裏唯一的男孩,自然能得到更多的資源。處於中間的我媽,本來就是幾兄妹中唯一的意外,穿着姐姐們穿舊的衣物,而到她的兩個妹妹時,衣服又剛好爛到不能穿,只得添置新的。
16歲那年,我媽從湖北陽新的老家來到福建晉江打工,那是她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鄉。
在閉塞的農村呆了16年,走過最遠的距離,便是翻過小山包去砍柴的路。生病了沒人管,幹活時總有她,唯一愜意的時候,便是閒下來後坐在凳子上,看看天邊的浮雲,看看飛過的小鳥,看看落下的紅日。她能接觸到的世界,僅有村挨村的一方天地,踏出村中的那一刻,便像被世界再次遺棄了。
那個時候,坐在前往異鄉的火車上,她感慨了一句:“這個世界像假的一樣。”
喫不飽穿不暖是常態,哪有心思去想七想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代際衝突,總被物質匱乏的大山壓在底下。

1980在搪瓷碗的碰撞中遠去,千禧年在諾基亞的喧囂中走來。
步入21世紀後,相對富足的物質生活讓人們有更多餘力去回應自己的精神追求,現代流行文化的湧入也助長了青少年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有着比七八十年代的農村孩童更加寬泛的眼界、更深層的認知。不再有既定的路徑依賴、不再被父母的三言兩語牽着鼻子走。
剛剛擺脫果腹蔽體之憂,隨即而來安心定神之慮。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兩代人的成長環境判若雲泥,兩代人對於各種事物的認知也截然不同。在難以逾越的代溝下,父母與子女的相處宛如演奏一曲酸甜苦辣並行的復調音樂
——在激烈爭吵中模糊了對方面目:一個貶成白眼狼,一個批成老頑固;
——在短暫和解後佩戴上一層面具:一個捧爲心肝命,一個奉爲好爸媽。
大雨傾盆之後未必就是太陽,激烈爭吵之後只有一地雞毛。

千禧年後的孩子在他們父母的眼中應當是幸福的,但卻成爲了我們口中迷茫的一代。時刻處於這種錯位中,低頭一看才發覺,自己此前一直在父母的唸叨中被推搡着。而現在,想自己走,卻苦於在時代的迷霧前一眼望不到頭。
我想起了艾米莉·迪金森的一首短詩,似乎能簡單地說明兩代人幸福觀念差異的緣由:
Had I not seen the Sun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I could have borne the shade
如果我不曾見過光明。
But Light a newer Wilderness
然而光明已使我的荒涼,
My Wilderness has made
成爲更新的荒涼。
——Emily Dickinson(1830-1886)
時代的十字路口,命運的千禧年,一代人在此處走向壯年,一代人在此時迎來新生。我們無需在一句又一句的爹味說教中去作兩代人苦難的比較,怒斥年輕人在閒碎時光的傷春悲秋。畢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艱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衷——正如那荒涼,已成爲更新的荒涼。

上一代人的苦痛離不開物質匱乏,這一代人的悲涼跳不脫精神壓抑。
許多人看來,在路遙筆下《平凡的世界》滿溢着的悲愴面前,千禧年後的青春傷痛文學彷彿無病呻吟。但不論是帶着厚重泥土氣息的苦難還是如煙塵般瑣碎的煩悶,在日積月累中,造成的傷害都難以估量。
有趣的是,《紙房子》用頗具時代特色的青春傷痛文學包裝,卻在對愛與恨的質詢中展現了不獨屬於一個年代的傷痛。
這份傷痛在貧窮的黃土大地上生根,在時代的快速變遷裏瘋長,它早在不知不覺荒蕪了一片地、葬送了一羣人。
窮苦年代的它是明槍下的暗箭,並非亟待解決的核心矛盾。當千禧年後生存的威脅逐步退場,圍繞親情的問題便大搖大擺地現身了。
這苦難從未厚此薄彼,它對兩代人的態度同樣無情。

曾經我聆聽母親的悲慘經歷,在不堪回首的往事中潸然淚下,深嘆物質匱乏年代對一個人的無情摧殘,在鑄造我媽堅強意志的同時,也留下了太多難以結痂的傷痕。
我過去膚淺地認爲身體上的苦難才令人難以忍受,後來愈發感到精神上的折磨更令人抓狂。其實母親那些難以結痂的傷痕不是來源於時代的暴行,而是物質匱乏處境下淡薄的親情。
親情在70/80後的童年中的存在普遍稀薄,而當他們成爲父輩時,竟又羣體失憶般地忘了“理解”二字在他們童年裏的分量,轉頭便在我們眼中變得如此不可理喻。
只得感嘆:時代發展的迅速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兩代之間被迅速地拉開了,中間隔着深深的溝壑。

代際衝突這個社會歷史背景深厚的結構性問題,是兩代人的共同困境。這便是爲何,明明是兩個時代,我卻由《紙房子》的故事想到了自己的母親。
兩代人困於同一種東西,又總在所困之物中互相傷害,從宏觀的角度看,似乎很愚蠢,然而身在其中,不能自已。
恨嗎?有時又恨不起來。愛嗎?從來談不上。
我始終對母親的這番關於對父母愛或恨的回應印象深刻,而到了《紙房子》中我又再見到了類似擰巴的情感。

然而我母親終歸是個好孩子了,這份擰巴的情感就一直這樣鬱結於心,除了我以外她似乎不願再提起。明明童年時收到的是最糟糕的對待,但如今她每個月給父母的錢,也並不比其他兄弟姐妹少。
趙穎也曾一直鬱結着,直到撫養的真相浮出水面,才終於引爆了埋在心底的那顆炸彈。
親情在哪個年代都能是最柔和的毛毯,厚實溫暖。而當它薄到成爲一把鋒利的快刀時,便戳穿了年代,以至於我竟置身於時代的十字路口前迷思良久。
人與人的悲歡並不相通,親情所繫卻永遠撥動人們的心絃,爲之同頻共振。
橫亙兩個年代的代際衝突,總在歷史煙雲中被人疏忽,可不論如何,兩代人通往幸福的路上,縱使殊途,也永遠要走過這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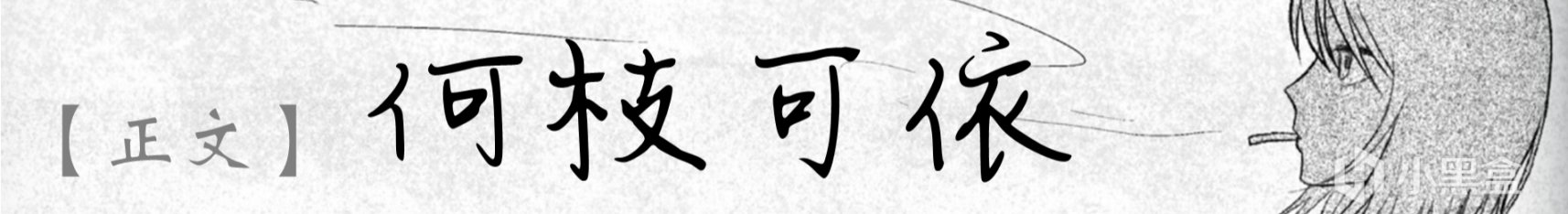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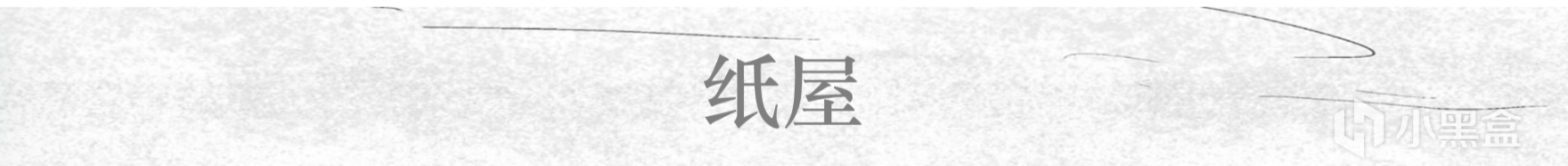
“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草窩。”對於舟車勞頓的人而言,家便是那個最能提供安逸與踏實的避風港。
可每當趙穎想安心地投入在家的懷抱中,先前如磐石般穩定堅固的房子就瞬間崩塌,提供不了半點支撐。
於她而言,這裏充其量是個能喫住的地方,分量輕如蠟紙,連父親落下的拳腳似乎都更重。
紙房子大抵就是如此,它能在風雨中被輕易打溼,也能在火光中被快速焚盡,當它消逝時甚至激不起一絲漣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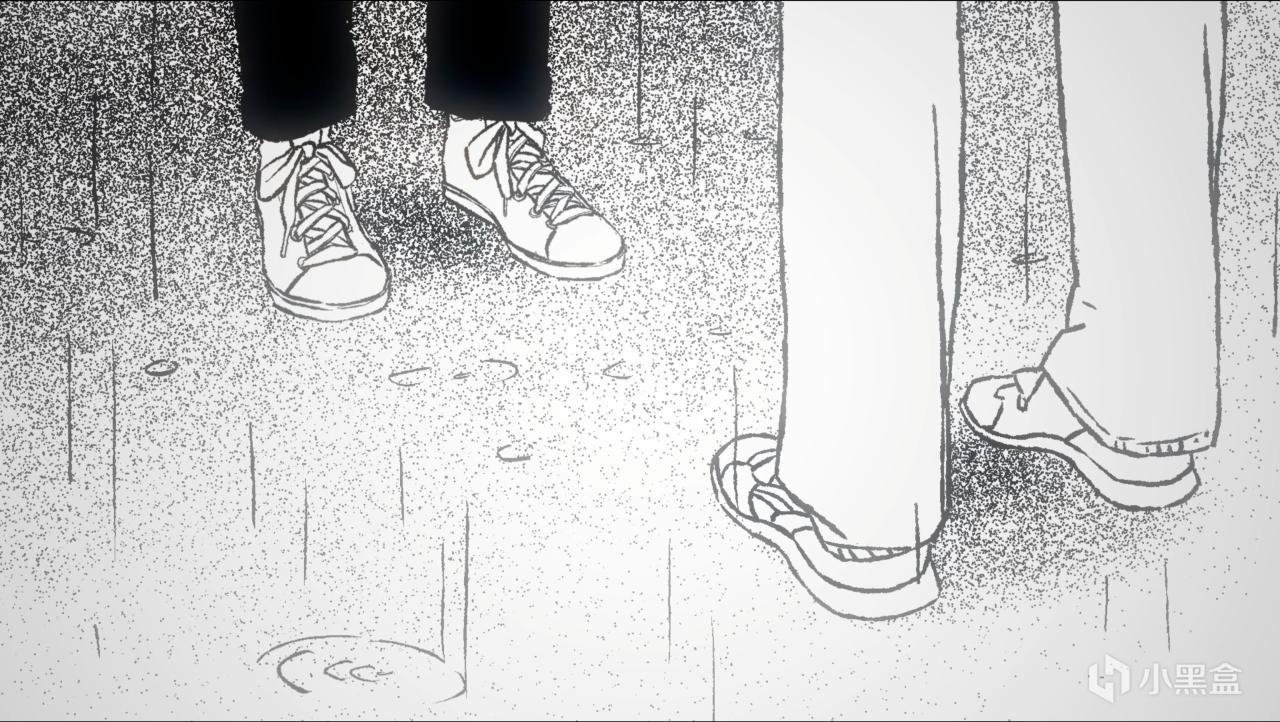
它冰冷、單薄,不帶任何情感色彩,甚至在看到這個遊戲名時,我的感受也像喝下一杯涼白開。
《紙房子》所展現是2018年西南邊陲一個不知名小鎮的圖景:老舊的樓房擠擠挨挨,烏泱泱一片。人們爲生活而奔走,行色匆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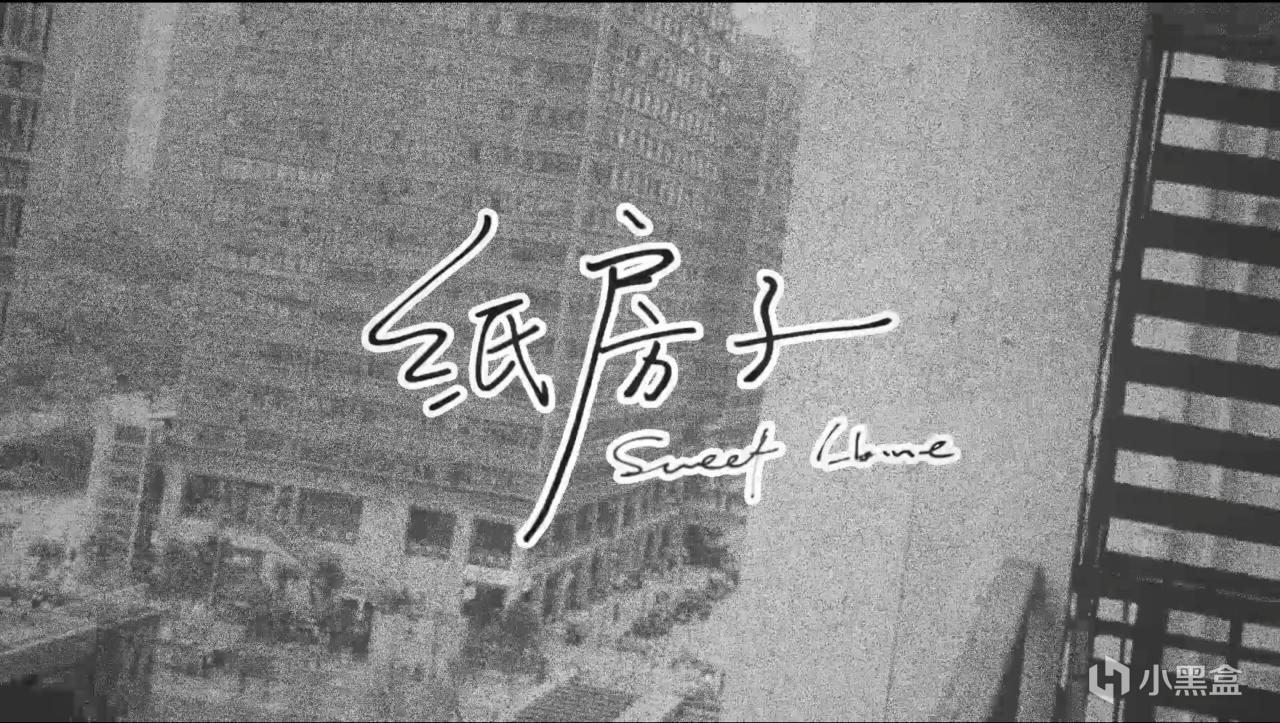
手繪風格的白紙黑線添了幾分庸碌的色彩,貼近生活的文本對話更讓人身臨其境。
00後能在其中回首學生時代的點點滴滴——閒情逸致摺疊的東南西北、課餘飯間談論的天涯海角,拼湊出那個在紙墨碰撞中變得迷離破碎的青澀時光。
正當你認爲這是一場對於往昔詩意的回首時,趙穎卻格格不入地出現在其中。
其他人打着雞血在教室爲高考拼搏的時候,她是電玩城的常客;其他人爲放學放假而興高采烈的時候,她叼根菸斜倚在牆邊。
她身邊的環境親切到讓人噁心,她身上的氣息疏離得讓人痛心。

泛白的臉頰傷痕累累,眼角的淚滴總拭不去。漫不經心的作態下,藏的是對生活缺了心、對未來失了意的唏噓事實。
正值青春的少女,怎會有這般死氣?像檐上的烏鴉,像缸中的灰燼。

上文我曾提到的,《紙房子》不獨屬於一個時代的傷痛,便在於此。
趙穎的死氣是傳統差序格局無法被輕易抹去的寫照,是畸形家庭結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的遺憾。
那把親情快刀在這樣的境況下帶給人重創,讓我們不得不扼腕嘆息。只得承認重組家庭難以迴避的問題,總是理所應當地成爲施暴者的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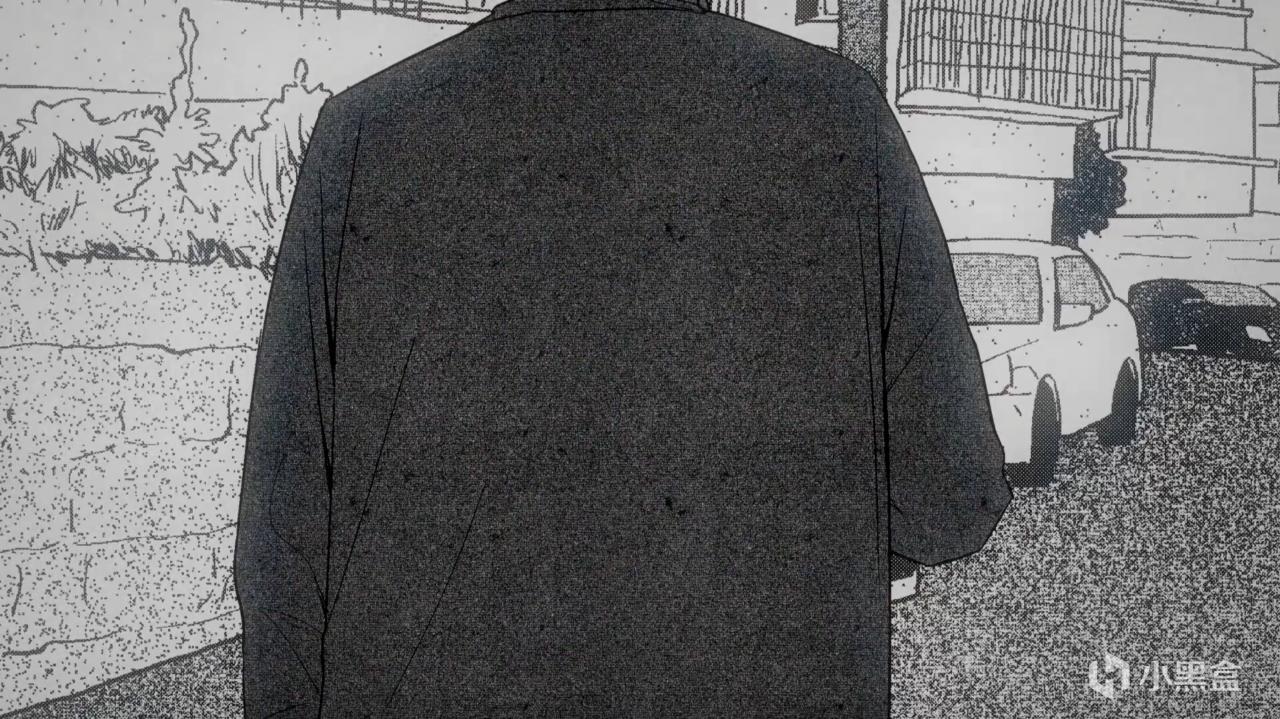
偏偏遊戲中趙穎的父親是個好面子的自私鬼,總執着於爲自己構建偉岸的形象,每當妻子不順遂無理取鬧的小女兒的意思,他便樂於駁斥妻子,既贏了尊嚴,又唱了白臉,還順帶捎上“好爸爸”的名號。
事實往往就是:趙子璇樂了,一個勁兒地重複父親支持的話語;妻子不記仇,幾分鐘後又冰釋前嫌。只有趙穎把父親的惺惺作態看在眼裏,每次觸目,那蠻橫的形象就又豐滿了幾分。

趙穎的父親不懂得教育,總自以爲是地將資源投入視爲最大的給予,而隨後所有的發展都要服從他的設想。他在語言溝通和情感傳遞上蹩腳地像個學生,慣用拳打腳踢“修正”子女的“錯誤”。他也不知道每一次的暴力行徑都在踩着趙穎的紅線,持續摧殘着本就脆弱不堪的心。

人從來是複雜多變的。《紙房子》中父親的形象之所以躍然紙上,在細膩且剋制的文字之後愈發讓人憎惡,不是因爲父親極致的扁平的壞,而恰恰是他的塑造立體、真實、有觸感。
他會在過年時塞紅包給趙穎,他會在丈母孃的臉色中安慰趙穎。
他總願墮落成一個畜牲,在你覺得該有情面的時候做的決絕,卻又在你心如死灰的時候冷不丁地突然像個人了。

這也是趙穎起初沒狠下心斷絕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冰冷的囚籠裏待久了,放風竟都會讓人激起感恩戴德之心。
也許趙穎就儘量不去想它了,她知道,寄託於紙房子從來都是無果的哀求。
隨後這一點便被馬上印證了,並且來得更加殘酷。父親那微不足道的態度搖擺也最終成了戲謔,爲自己挖好名爲仇恨的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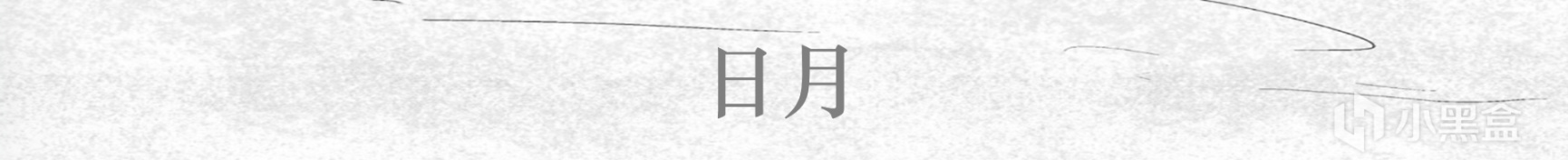
好在趙穎還有朋友,讓她的心有更多寄存之地,不至於僅剩那輕飄飄的紙房子,屋漏偏逢連夜雨般走向毀滅。
同齡的朋友一位像太陽,一位像星星,剛認識的那個,似乎是時圓時缺的月亮。
【太陽】
王藝菡便是那個毋庸置疑的太陽,光明、澄澈,沒有一絲雜質,以至於這個幾乎對誰都要先亮出一身刺的豪豬(趙穎),都在這足以淨化心靈的陽光中收起了自己的敵意。
“Elle est si faible! Et elle est si naïve. Elle a quatre épines de rien du tout pour la protéger contre le monde...”
“她是那麼弱小!又是那麼天真。她只有四根微不足道的刺來保護自己,對抗整個世界……”
——《小王子》,聖埃克蘇佩裏
這個太陽實在太過耀眼,哪怕最乾澀的眼也得擠下幾滴淚。

王藝菡於趙穎不僅是諸如電玩城包票的物質支持者,更是撫慰心靈的精神良藥。
她靜靜地聆聽趙穎的苦難,但從未以施捨的形式給予同情,而是將自己與趙穎捆綁起來,如同行共渡的旅人。
她們的境遇差異,大到像活在兩個不同時代的人。王藝菡能收穫長輩無微不至卻又不濫成溺愛的關照,她家的富裕足以讓其肆意揮霍瀟灑人生,趙穎卻只能爛在角落裏發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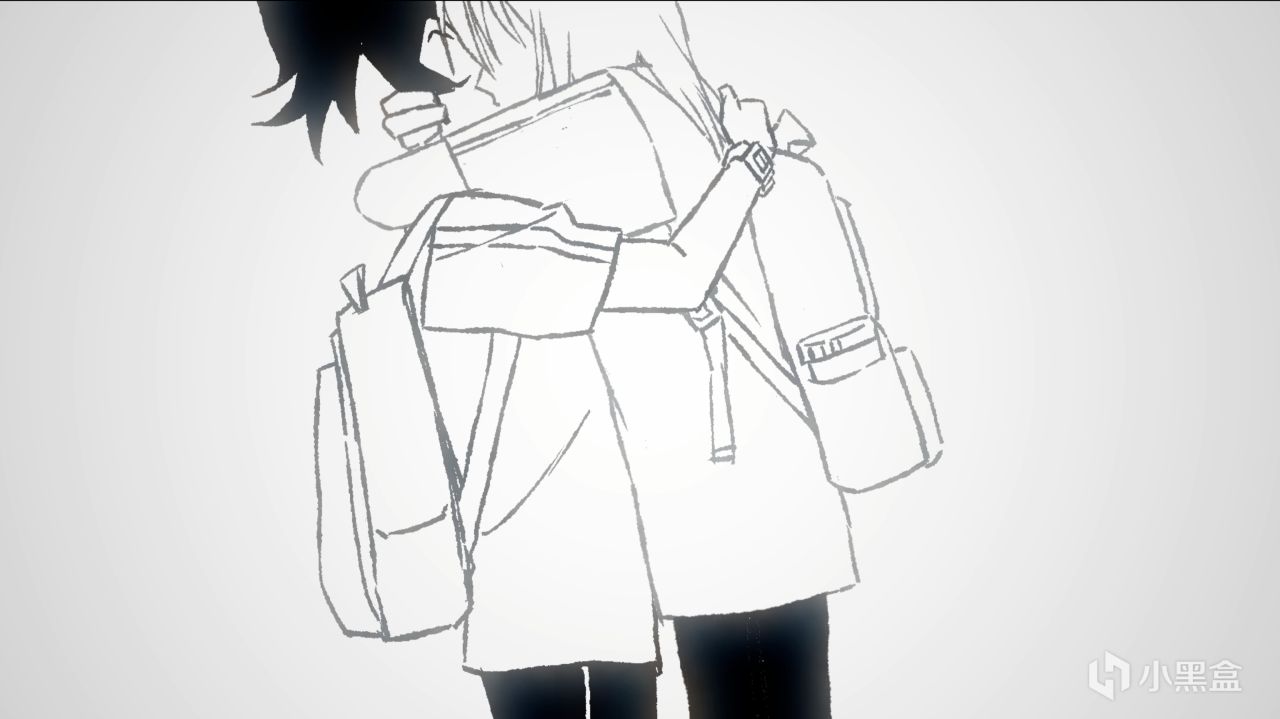
王藝菡有愛人的心、愛人的資本、愛人的氣量,這使得她能夠對摯友幾乎毫無保留地敞開自己的一切,除了那在稚子之心下也無法跨越的界限——同性之間的愛戀。
她的純粹是如此極致,既願在山峯與溝壑的落差中力挽狂瀾,也能在友情與愛情的含糊裏涇渭分明。
她用光用熱,爲趙穎驅散黑暗、逼走寒冷,是製作組留給趙穎的溫柔一筆。
只可惜,若非趙穎在家庭苦難的話題中有所保留,王藝菡便有更多的機會完成對於一個破碎心靈的救贖。

【星星】
雖爲摯友,但相比王藝菡,周喜在趙穎的苦難敘事中便曖昧不明瞭,她多數時候扮演的是一個調節氣氛角色,帶給趙穎歡笑與淚水,但她始終沒有深入趙穎真正創傷的內心世界,遊戲中也沒有周喜的劇情線。她僅是遠處的星星,有光,但渺茫,有熱,但難及。在此便不贅述了。

【月亮】
月之女神塞勒涅曾乞求宙斯:
Ἀσπάσιον δέ οἱ εἶδος ἐπ’ αἰωνίῳ ὕπνῳ καλὸν αὑτοῦ ζωὸν ἀποκρύπτειν ἐνὶ σπήλυῳ.
“讓他(恩底彌翁)在永恆的睡眠中,將他可愛的容貌藏於一個山洞裏,只爲她一人所有。”
走陸婷線的時候,我總想到希臘神話中月之女神塞勒涅扭曲的、強欲的愛,她阻止任何事物從她身邊奪走恩底彌翁,哪怕時間,爲此甚至不惜將其變爲永凍的雕塑。

三相變化的月,時圓時缺,似乎也能很好地描述陸婷時好時壞的情緒狀態。在外人看來,這個性格怪異的女孩實在難以接近,源於家庭的自卑性格讓她明明有着一顆想要結交好友的心,但卻總在他人的搭話中沉默以對。
她和趙穎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互補,她們各自都有原生家庭帶來的苦難,但這種苦難並不相同,她們的脆弱之處也因此迥異。趙穎的苦痛深藏於心,陸婷的病態暴露無遺。

外婆摳摳搜搜,對陸婷人生的窺探和干預似乎從未停歇,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演變成漫長的口舌之災。
在本就貧窮而擁堵的成長環境下,這樣令人窒息代際關係如同雪上加霜,使得陸婷的自卑感越發強烈。一方面,她總將事情發展過程的偏離歸咎於自身的過錯,另一方面,當自己對某事物求而不得之時,她會想盡辦法據爲己有以裝點自己那可悲的自尊——不論這動機是仇恨的報復還是扭曲的愛。

她偷竊憎惡之人日常使用的器物,享受仇恨得報自我勝利的快感。
她偷竊愛慕之人促膝言歡的幸福,深陷求而不得自我否定的泥潭。
她的心胸已經被生活、家庭和社會壓得夠狹隘,眼裏只剩下極化的對錯親疏。

親近小動物,是因爲只有當面對弱小生靈時,自己才能短暫地忘卻一切恐懼與自卑,展露出最質樸真實的歡笑。
而到了面對人時,她慣性地將自己視作被圈養的牲畜——於是舉止如過街的老鼠,在被歧視妄想的心態中,以最卑微的姿態出現在他人的視野。
要靠疼痛來體味活着的觸感,要用獨佔來彰顯友誼的純粹。就連飽經苦難的趙穎在他身邊時,都不由得感嘆——世界上原來不止有那一種痛苦。

她對趙穎由恨生愛,而後與趙穎難得的友誼又迅速在扭曲的情感中趨於變質,只等那個“愛否”的回答一錘定音——她的人生早就被趙穎所左右了。
只要那個無情的拒絕脫口而出,陸婷便可以馬上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
那麼接受陸婷的愛又有何緣由?或許是趙穎在徐敏敏處驗證過的性取向,又或許只是在重組家庭傷害後病急亂投醫的湊合……
這愛情後面註定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畸形、扭曲,引人垂憐。
她就像飛蛾,急不可耐地尋求自己的光明,往往在撲火的癲狂中走向毀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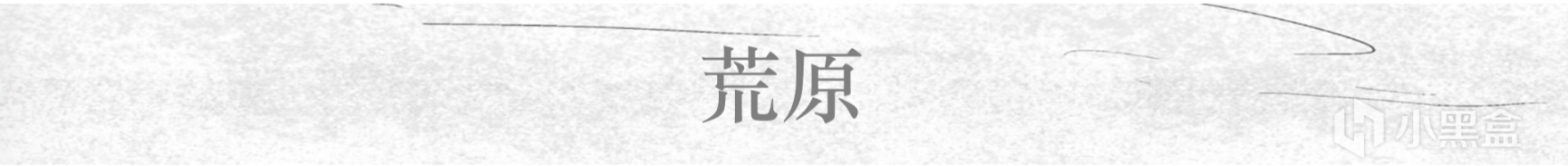
我寧願是被媽媽拋棄的孤兒,也不願當他們家裏多餘的東西。
趙穎對那虛假家庭的忍耐終有極限。
在一個世界線,總於菸灰缸中沉寂的煙炱,終於從菸蒂蔓延到那個糟糕的重組家庭。
那個錯失王藝菡的最後救贖的夜晚,迎來了一個屬於沉默者的爆發。

從來都是被送出家門的趙穎,今天便來了一個小小的回敬——將重組家庭送進自己準備的墳墓。漫天的火光吞噬了那個她曾居住的、被稱爲家的地方。與之鮮明對照的,一處冰冷的旮旯中,趙穎癱坐在地上。
結束了,這一切終於結束了……然後呢?
這個我們看來相較於其它Ending而言比較悲慘的結局,其實已經是最現實的結局,不,可能甚至會好上一些,畢竟煙花綻放的那一刻,是美麗的。曇花一現,也比黯淡一生充實。

這時代無法迴避的問題,就這樣於個例的火光中映照出身後無數個“趙穎”的影子,隨即消防救護的鳴笛爲其畫上最諷刺的句號。
一個病態的家庭在火焰中毀滅,千千萬萬個受了傷的失語者才藉此出了聲,那麼時代車輪碾過的滿地狼藉,還有多少在沉默中消逝的悲劇?它們的聲音甚至都尚在乾澀的喉嚨中打着旋,還未來得及嘶吼出來,便已化爲枯骨。

我們再看那冷卻的菸灰、破碎的酒瓶,似乎就是他們曾經存在的最有力寫照。
“在試圖建立保護罩的過程中,受害者可能變得對‘喚起’(arousal)本身產生恐懼。他們可能會通過迴避一切可能喚起情緒的情境來麻木自己的內在體驗。使用酒精、毒品或自我飢餓(如進食障礙)可以達到此目的。雖然這些方法可能提供暫時的緩解,但最終它們會通過促成一種持續的過度警覺和侵入性症狀的狀態,而加劇創傷後綜合徵。因此,受害者抵禦侵入性症狀的努力,最終變成了這些症狀本身的一個主要來源。”
——《創傷與復原》,朱迪斯·赫爾曼
起先,那煙並不承載着什麼,直到臉上痛感越來越重,麻木的四肢愈發冰冷,那煙就戒不掉了,而人也再難逃出生活的泥沼。

抽刀斷水,舉杯消愁。停不下的吞雲吐霧背後,除了個人情感的顛沛流離,還有時代光明未能穿透黑暗的難言之隱。
在不爲人知的角落,代際的問題愈發畸形,紙房子也一次又一次在烈火中燃盡。
那麼,燒了這紙糊的房子,又有何枝可依?
縱使有天地爲家的豪邁,未必找得到那個能伴你一生慢行的日月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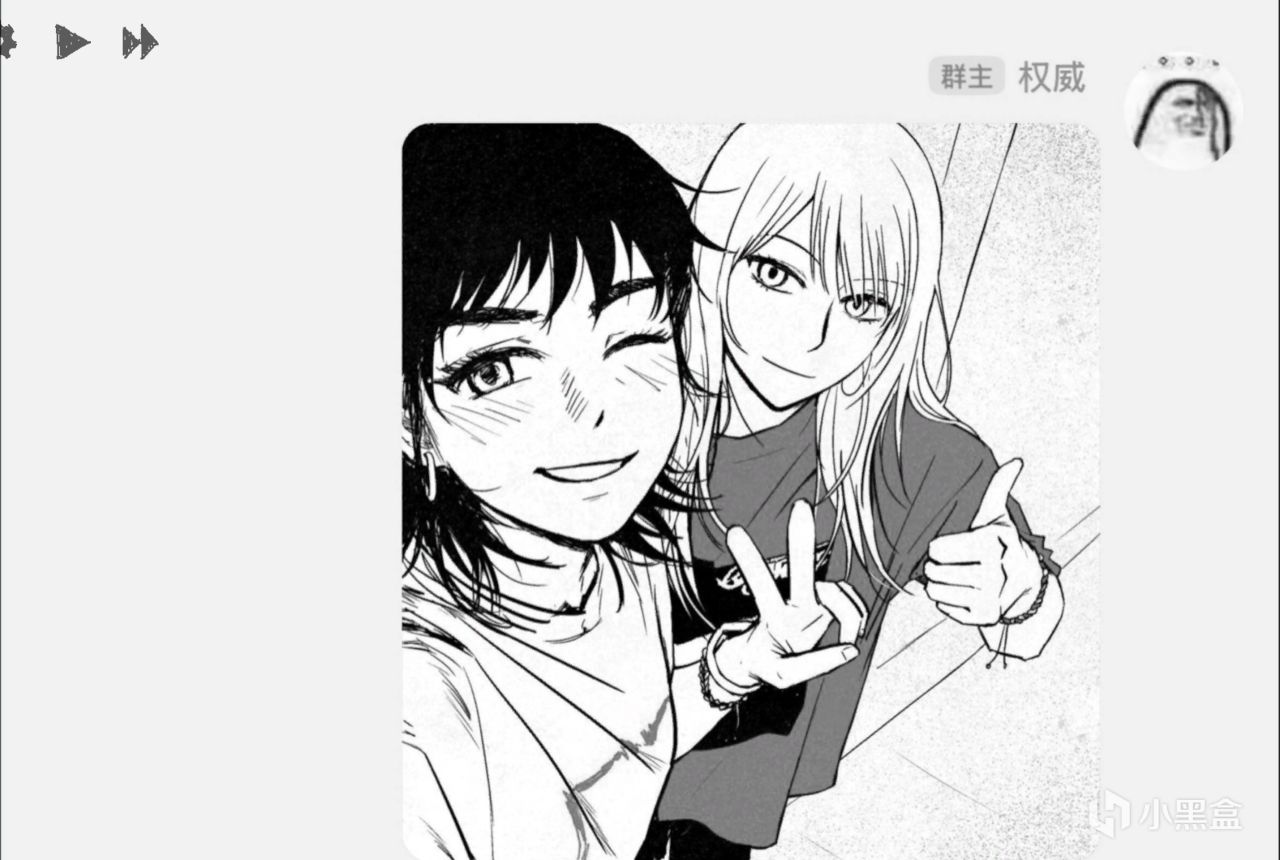
趙穎有她的太陽,更有可託付的老師,然而一切都是那麼容易失之交臂。
能讀檔尚且容易錯過一個個愈療的契機,現實裏單向的人生,談何容易?況且,時代的裹挾中,很多選擇往往身不由己。
我不再沉醉於遠走高飛的幻夢,不再輕視那燼滅缸中的菸灰。
幻夢離現實太遠,菸灰卻從屏幕內一把扼住人們鼓動的心臟,讓人不由得屏住呼吸,沉浸地聆聽屬於萬千個趙穎的故事。
《紙房子》的吶喊,無疑是振聾發聵的。我們也在這吶喊聲中,一遍又一遍地問出那個問題:
“趙穎,到底要怎樣你才能幸福……”
起初那是滿帶好奇的疑問,一曲終了,那疑問也變成了嘆息。
紙屋易燼,荒土難花。此刻不再僥倖,惟願一切安好。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