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深夜中,Y先生與妻子在一次親密行爲中,失手將妻子掐至昏迷。當妻子醒來後,用鄰居電話報了警把Y先生領走並帶去了精神病醫院。在醫院中,Y先生說他對自己攻擊了妻子感覺很懊惱,但是也對妻子不佩戴婚戒很生氣。然後他堅持要離開醫院,並宣稱不會再去傷害他的妻子,因爲他相信妻子會回到他身邊。但他的妻子已經離開他了。在心理評估中心,評估師預見到Y先生一旦幻想破滅,他“殺戮性的憤怒”很可能會重現。於是陪同在醫生的護士開了臨時留院單,可是被Y先生拒絕。
稍後在同一天,政府篩查員來看望時,Y先生仍然聲稱自己很懊悔並對自己做的事情感覺很愚蠢。然而,篩查員卻否認了這份專業的心理評估報告,對其中關於Y先生“幻想式否認”的警告置之不理,並且拒絕了批准對Y先生的初步強制性留院申請。
因此,Y先生回家了。稍後他開車去了他岳母家,他妻子所住的地方。當時他的妻子正在遛狗,他走向妻子並跟她說話,試圖說服她跟他一起回家。當妻子拒絕他的請求並且開始逃開時,他朝她背後開槍,將她殺死了。隨後,他一個人在一間汽車旅館房間裏,開槍自殺。
Y先生的故事是一個極端但深刻的警示。它揭示了一種強大、原始且無處不在的心理力量——“否認”(Denial)。它不同於簡單的“不同意”或“嘴硬”,而是一種能夠重塑現實、甚至帶來毀滅性後果的心理防禦機制。Y先生的悲劇並非孤例,他的“否認”並非只存在於他個人內心。政府篩查員可能是爲了避免過於麻煩的手續或者自以爲是的認知認爲Y先生僅僅是有一點焦慮,從而也否認了心理醫生的專業判斷。這種“否認的社會性傳染”最終導致了整個系統的失靈,將一個本可干預的危機推向了無可挽回的終點。
那麼,這種名爲“否認”的心理力量,究竟是如何在我們內心運作,甚至操縱我們的現實的?本文將帶你深入精神分析的腹地…...
一.定義:心靈的“鴕鳥”
什麼是“否認”?美國心理學會(APA)給出的官方定義是:一種防禦機制,個體通過它無意識地忽略或排除那些令人不快的想法、感受、願望或事件,使其無法進入意識層面。這種機制旨在解決情感衝突或減輕焦慮 。
精神分析的開創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形象地將其描述爲一種“鴕鳥政策”(ostrich policy)。如同傳說中鴕鳥遇到危險時會把頭埋進沙子,以爲看不見危險就不存在一樣,啓用“否認”機制的個體,也在心理層面上拒絕感知那些會引發痛苦的外部現實。

鴕鳥遇到危險時(圖片來源於網絡)
“否認”之所以被視爲一種相對原始的防禦機制,關鍵在於它與其他防禦方式的本質區別。例如,“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承認事實,但爲其尋找一個可接受的解釋(“我考試沒過,是因爲老師考的知識點我恰好沒複習到”);“投射”(Projection)也是承認某種感受存在,但將其歸於他人(“不是我恨他,是他恨我”)。這些機制都在一個已然被感知的現實基礎上進行二次加工。
而“否認”則更爲根本,它試圖從源頭上拒絕現實本身進入意識。它不是在解釋現實,而是在宣佈“這不是現實“。這種對現實的直接摒棄,使其成爲一種強大但風險極高的防禦策略,因爲它切斷了個體與真實世界的聯繫,彷佛是你在水杯中倒水之前,首先否認了水杯的存在。
二.“否認”演化史
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更關注“壓抑”,即”自我“。將來自”本我“的、不爲”超我“所容的內部衝動(如攻擊性、性慾)壓入無意識的過程。然而,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另一種防禦形式,並用德語詞“Verleugnung”(英文常譯爲Disavowal,否認/否認)來描述它。這個概念指的是拒絕承認某個令人痛苦的外部現實。這標誌着精神分析開始認識到,自我的防禦不僅針對內部的慾望,也針對外部世界的真相。
真正將“否認”提升到核心防禦機制地位的是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3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自我與防禦機制》中系統地梳理了包括“否認”在內的十種主要防禦機制 8。通過對兒童的細緻觀察,安娜·弗洛伊德發現,孩子們會頻繁地使用“幻想中的否認”和“言語和行爲上的否認”來應對自己無力改變的外部環境,例如,一個害怕嚴厲父親的孩子,可能會在幻想中把父親想象成一隻保護自己的動物。這一貢獻極大地推動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學”轉向,理論的焦點從本我的原始驅力,更多地轉移到了自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掙扎、適應與成長的過程。
當代對防禦機制的理解,深受美國精神病學家喬治·瓦利恩特的影響。通過長達數十年的縱向研究,瓦利恩特不再將防禦機制視爲一個簡單的列表,而是構建了一個基於“成熟度”的層級模型。在這個模型中,防禦機制被分爲四個層級:
第一級:病理/精神病性防禦(如精神病性否認、歪曲)
第二級:不成熟防禦(如投射、被動攻擊、否認)
第三級:神經症性防禦(如理智化、反向形成、壓抑)
第四級:成熟防禦(如幽默、昇華、利他)
瓦利恩特明確地將“否認”歸爲不成熟的防禦機制。他的研究用大量實證數據表明,成年後若過度依賴使用“否認”,這與較差的社會適應,困難的人際關係以及更高的精神病病理風險顯著相關 。瓦利恩特的工作,無疑是將精神分析理論從問診室帶向了可被經驗數據檢驗的科學領域,也爲成長中的心理健康帶來更爲動態、發展的視角。
三.否認的千副面孔
一般來說,否認分爲四種類型:本質否認、行動上的否認、言語與行爲相悖的否認、幻想中的否認。我們分別來看看
1. 本質否認(Essential Denial)
這是最直接的否認形式,即完全拒絕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典型案例:一個長期酗酒者,儘管已經出現了健康問題、家庭矛盾和工作失誤,但他依然堅稱:“我沒有酗酒,我只是喜歡喝幾杯,隨時都能停下來。”。
2. 行動上的否認(Denial in Action)
這種否認不一定通過語言表達,而是通過與現實完全相悖的行爲來體現。”
典型案例:一位企業主的公司已經瀕臨破產,銀行正在催收貸款,但他卻在此刻耗費巨資重新裝修辦公室,舉辦盛大的慶功派對。他的行爲傳遞的信息是:”我的公司蒸蒸日上,危機並不存在。”
3. 言語與行爲相悖的否認(Denial in Word and Act)
這是一種更復雜、更具迷惑性的否認。個體在口頭上可能承認問題的存在,但其後續行爲卻完全否定了這份“承認”。
典型案例:一位家長可能會對朋友抱怨:“我真的覺得孩子太過於沉迷手機等電子產品,對眼睛不太好。”然而,一回到家,爲了換取片刻的安寧,他仍然會毫不猶豫地把平板電腦遞給哭鬧的孩子。這裏的口頭承認,更像是一種社交姿態或瞬間的焦慮釋放,而非真正內化的現實。
4. 幻想中的否認(Denial in Fantasy)
當外部世界過於痛苦而無法承受時,個體可能會退縮到一個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內心幻想世界中,以此來否認和替代現實。
典型案例:二戰後,納粹德國的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在紐倫堡法庭上接受審判。面對戰爭罪行的鐵證和即將到來的死刑,他常常在法庭上閉上眼睛,在腦海中重溫自己過去作爲帝國元帥的輝煌歲月、盛大的派對和民衆的歡呼。通過沉浸在幻想中,他暫時“否認”了自己已是階下囚的屈辱現實。
四.“否認”爲何以及如何形成?
理解了否認是什麼之後,往下則更深入探究爲何否認會形成以及如何形成。
1.爲何形成?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否認”是“自我”爲了保護自身完整性而啓動的緊急程序。當個體面臨的焦慮感過於強烈,以至於有壓垮心智的危險時,“自我”就會介入。這種壓倒性的焦慮可能源於兩個方面:
外部威脅:如突如其來的死亡診斷、毀滅性的失業通知、親人的背叛等。這些外部事件直接衝擊了個體的安全感和存在感。
內部衝突:即“本我”的原始衝動(如我好想澀澀!)與“超我”的道德戒律(如“我要戒色,澀澀是不對的!”)之間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兩種情況下,“自我”作爲心靈的協調者,如果無法通過更成熟的方式(如解決問題、尋求支持)來化解焦慮,就可能採取最簡單粗暴的方式——關閉感知的閥門,直接“否認”焦慮源的存在,從而暫時維持內心的和平。
2.如何形成?
現代認知心理學爲我們揭示了“否認”在信息處理層面的具體運作方式。它並非一個神祕的過程,而是一系列認知偏差和信息過濾策略共同作用的結果。
注意力偏差:個體會有選擇地避開那些可能引發痛苦的信息源。比如,一個懷疑自己患病的人可能會刻意迴避所有與該疾病相關的文章和新聞。
解釋偏差:當無法迴避負面信息時,個體會將其重新解釋爲無害的。例如,一個在戀愛關係中遭遇冷暴力的人,可能會將對方的漠視解釋爲“他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
記憶偏差:對於已經發生的創傷性事件,大腦可能會通過遺忘的方式來“否認”其發生過,這在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中尤爲常見。
此外,一些普遍的認知偏見也爲“否認”的形成提供了溫牀,例如“證實性偏見”,即人們傾向於尋找、解釋和回憶那些支持自己既有信念的信息;以及“樂觀偏見”,即人們傾向於認爲負面事件更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否認”並非一種被動的“視而不見”,而是一種主動的、持續消耗心理能量的現實構建過程。弗洛伊德的動力模型早已暗示,自我需要耗費能量才能將現實擋在意識門外。現代神經科學的研究也發現,維持否認狀態可能需要大腦前額葉皮層對杏仁核等情緒中樞進行主動抑制,這是一種活躍的神經活動。那些爲自己的否認尋找理由、指責他人、迴避話題的行爲,都是在積極地維護那個被自己扭曲了的“現實“。這解釋了爲何長期處於否認狀態的人會感到疲憊,也解釋了當否認的堤壩最終崩潰時,現實的洪流會帶來如此巨大的衝擊。
四. 現實中的“否認”:從家庭生活到網絡論戰
舉一個生活中的例子
小明曾是父母的驕傲,成績優異,是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但進入高中後,他的成績開始下滑,變得沉默寡言,對練習兩年半的籃球也提不起興趣。父母看在眼裏,急在心裏。老師建議他們帶小明去看看心理醫生,懷疑他有抑鬱傾向。
然而,小明的父母對此的反應是典型的“否認”。他們可能會說:“男孩子嘛,到了青春期都這樣,過陣子就好了。”或者將原因歸咎於外部:“肯定是學校壓力太大了,換個環境就好了。”他們拒絕接受“兒子可能心理生病了”這個現實,因爲這會嚴重衝擊他們“成功父母”的自我認同。這種否認,讓他們錯過了最佳的干預時機,小明的狀況也因此可能進一步惡化。在這個家庭系統中,父母的否認像一層密不透風的膜,將外界的幫助和孩子求救的信號都隔絕在外。
再舉一個網絡現象:“鴕鳥心態”
這個詞彙用來形容那些主動迴避負面信息、假裝問題不存在的行爲。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心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術加持。算法構建的“信息繭房”和“迴音壁”,使得持特定觀點的人可以輕易地屏蔽掉所有相反的證據,只看到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
在過去,一個人的否認需要消耗巨大的心理能量來對抗來自周圍世界的不同聲音。而在網絡上,一個人可以輕易找到成千上萬的夥伴,共同構建一個強大的“否認”堡壘。在這個堡壘裏,否認不再是個體的防禦,而是一種集體的身份認同。任何試圖挑戰這種否認的外部信息,都會被視爲來自“敵對陣營”的攻擊,從而被更加堅決地排斥。這使得互聯網讓原本孤立的個人防禦,演變成了堅不可摧的集體幻覺,也解釋了爲何當今許多網絡爭端如此兩極分化且無法調和——人們捍衛的早已不是事實,而是那個被集體所驗證的、用以否認不安現實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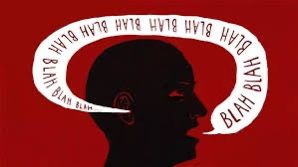
信息繭房的人們
五. 否認一定是錯誤的嗎?
我一直貫徹的理念是,沒有任何一種防禦機制是錯誤的,只有“固着”是錯誤的。當我們固着了“否認”,成爲一種長期、僵化的生活方式,它就會阻礙問題的解決、破壞人際關係、扼殺個人成長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而我們靈活運用“否認”,比如面對親人的去世,短暫的否認就是在爲我們爭取接納現實的時間,維持人格的穩定。我們必須要問自己:我們否認的是不可改變的過去,還是需要我們行動的現在與未來?如果發現自己成癮於某件壞的事情還在持續否定,這就是在阻礙改變的發生,逃避自己的責任!
六. 將頭從沙土抬起,直面真實的自己
我們見證了Y先生的悲劇,小明家庭的悲哀,網絡上信息繭房下極端人羣的可笑,我們發現,“否認”作爲一種最古老的心理防禦,始終與人類的焦慮和恐懼相伴而行。它愚蠢但是又何其忠誠,在我們最脆弱的時候挺身而出,爲我們抵擋那些無法承受的真相。
不過,我們無需將其視爲一個需要徹底根除的敵人。相反,我們應該學會將它看作一個信號——一個提醒我們內心正在經歷巨大風暴的信號。
真正的成長,始於我們將頭從沙土中抬起的那一刻。這意味着培養自我覺察的能力,誠實地審視自己的行爲和想法,分辨我們的“否認”究竟是在提供必要的緩衝,還是在構築逃避的牢籠。這意味着鼓起勇氣,去面對那些我們一直迴避的真相,無論是關於我們的健康、我們的關係,還是我們自己。
當然,有些真相過於沉重,我們無法獨自承受。這時,向信任的家人、朋友或專業的心理諮詢師求助,就顯得至關重要。他們可以成爲我們重返現實的嚮導和支撐。或許你可以嘗試向一個你完全信任的人,說出一件你一直在迴避的小事
最終我們將擁抱現實,即使它不完美,甚至充滿痛苦,但唯有在真實的大地上,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靜、堅韌與自由,甚至連“復仇”也有選擇的權利。
如果看到這裏覺得還不錯不妨點點贊,點點關注,你們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動力!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