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深夜中,Y先生与妻子在一次亲密行为中,失手将妻子掐至昏迷。当妻子醒来后,用邻居电话报了警把Y先生领走并带去了精神病医院。在医院中,Y先生说他对自己攻击了妻子感觉很懊恼,但是也对妻子不佩戴婚戒很生气。然后他坚持要离开医院,并宣称不会再去伤害他的妻子,因为他相信妻子会回到他身边。但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他了。在心理评估中心,评估师预见到Y先生一旦幻想破灭,他“杀戮性的愤怒”很可能会重现。于是陪同在医生的护士开了临时留院单,可是被Y先生拒绝。
稍后在同一天,政府筛查员来看望时,Y先生仍然声称自己很懊悔并对自己做的事情感觉很愚蠢。然而,筛查员却否认了这份专业的心理评估报告,对其中关于Y先生“幻想式否认”的警告置之不理,并且拒绝了批准对Y先生的初步强制性留院申请。
因此,Y先生回家了。稍后他开车去了他岳母家,他妻子所住的地方。当时他的妻子正在遛狗,他走向妻子并跟她说话,试图说服她跟他一起回家。当妻子拒绝他的请求并且开始逃开时,他朝她背后开枪,将她杀死了。随后,他一个人在一间汽车旅馆房间里,开枪自杀。
Y先生的故事是一个极端但深刻的警示。它揭示了一种强大、原始且无处不在的心理力量——“否认”(Denial)。它不同于简单的“不同意”或“嘴硬”,而是一种能够重塑现实、甚至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心理防御机制。Y先生的悲剧并非孤例,他的“否认”并非只存在于他个人内心。政府筛查员可能是为了避免过于麻烦的手续或者自以为是的认知认为Y先生仅仅是有一点焦虑,从而也否认了心理医生的专业判断。这种“否认的社会性传染”最终导致了整个系统的失灵,将一个本可干预的危机推向了无可挽回的终点。
那么,这种名为“否认”的心理力量,究竟是如何在我们内心运作,甚至操纵我们的现实的?本文将带你深入精神分析的腹地…...
一.定义:心灵的“鸵鸟”
什么是“否认”?美国心理学会(APA)给出的官方定义是:一种防御机制,个体通过它无意识地忽略或排除那些令人不快的想法、感受、愿望或事件,使其无法进入意识层面。这种机制旨在解决情感冲突或减轻焦虑 。
精神分析的开创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形象地将其描述为一种“鸵鸟政策”(ostrich policy)。如同传说中鸵鸟遇到危险时会把头埋进沙子,以为看不见危险就不存在一样,启用“否认”机制的个体,也在心理层面上拒绝感知那些会引发痛苦的外部现实。

鸵鸟遇到危险时(图片来源于网络)
“否认”之所以被视为一种相对原始的防御机制,关键在于它与其他防御方式的本质区别。例如,“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承认事实,但为其寻找一个可接受的解释(“我考试没过,是因为老师考的知识点我恰好没复习到”);“投射”(Projection)也是承认某种感受存在,但将其归于他人(“不是我恨他,是他恨我”)。这些机制都在一个已然被感知的现实基础上进行二次加工。
而“否认”则更为根本,它试图从源头上拒绝现实本身进入意识。它不是在解释现实,而是在宣布“这不是现实“。这种对现实的直接摒弃,使其成为一种强大但风险极高的防御策略,因为它切断了个体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彷佛是你在水杯中倒水之前,首先否认了水杯的存在。
二.“否认”演化史
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更关注“压抑”,即”自我“。将来自”本我“的、不为”超我“所容的内部冲动(如攻击性、性欲)压入无意识的过程。然而,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另一种防御形式,并用德语词“Verleugnung”(英文常译为Disavowal,否认/否认)来描述它。这个概念指的是拒绝承认某个令人痛苦的外部现实。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开始认识到,自我的防御不仅针对内部的欲望,也针对外部世界的真相。
真正将“否认”提升到核心防御机制地位的是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3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自我与防御机制》中系统地梳理了包括“否认”在内的十种主要防御机制 8。通过对儿童的细致观察,安娜·弗洛伊德发现,孩子们会频繁地使用“幻想中的否认”和“言语和行为上的否认”来应对自己无力改变的外部环境,例如,一个害怕严厉父亲的孩子,可能会在幻想中把父亲想象成一只保护自己的动物。这一贡献极大地推动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转向,理论的焦点从本我的原始驱力,更多地转移到了自我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挣扎、适应与成长的过程。
当代对防御机制的理解,深受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的影响。通过长达数十年的纵向研究,瓦利恩特不再将防御机制视为一个简单的列表,而是构建了一个基于“成熟度”的层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防御机制被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级:病理/精神病性防御(如精神病性否认、歪曲)
第二级:不成熟防御(如投射、被动攻击、否认)
第三级:神经症性防御(如理智化、反向形成、压抑)
第四级:成熟防御(如幽默、升华、利他)
瓦利恩特明确地将“否认”归为不成熟的防御机制。他的研究用大量实证数据表明,成年后若过度依赖使用“否认”,这与较差的社会适应,困难的人际关系以及更高的精神病病理风险显著相关 。瓦利恩特的工作,无疑是将精神分析理论从问诊室带向了可被经验数据检验的科学领域,也为成长中的心理健康带来更为动态、发展的视角。
三.否认的千副面孔
一般来说,否认分为四种类型:本质否认、行动上的否认、言语与行为相悖的否认、幻想中的否认。我们分别来看看
1. 本质否认(Essential Denial)
这是最直接的否认形式,即完全拒绝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典型案例:一个长期酗酒者,尽管已经出现了健康问题、家庭矛盾和工作失误,但他依然坚称:“我没有酗酒,我只是喜欢喝几杯,随时都能停下来。”。
2. 行动上的否认(Denial in Action)
这种否认不一定通过语言表达,而是通过与现实完全相悖的行为来体现。”
典型案例:一位企业主的公司已经濒临破产,银行正在催收贷款,但他却在此刻耗费巨资重新装修办公室,举办盛大的庆功派对。他的行为传递的信息是:”我的公司蒸蒸日上,危机并不存在。”
3. 言语与行为相悖的否认(Denial in Word and Act)
这是一种更复杂、更具迷惑性的否认。个体在口头上可能承认问题的存在,但其后续行为却完全否定了这份“承认”。
典型案例:一位家长可能会对朋友抱怨:“我真的觉得孩子太过于沉迷手机等电子产品,对眼睛不太好。”然而,一回到家,为了换取片刻的安宁,他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把平板电脑递给哭闹的孩子。这里的口头承认,更像是一种社交姿态或瞬间的焦虑释放,而非真正内化的现实。
4. 幻想中的否认(Denial in Fantasy)
当外部世界过于痛苦而无法承受时,个体可能会退缩到一个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内心幻想世界中,以此来否认和替代现实。
典型案例:二战后,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法庭上接受审判。面对战争罪行的铁证和即将到来的死刑,他常常在法庭上闭上眼睛,在脑海中重温自己过去作为帝国元帅的辉煌岁月、盛大的派对和民众的欢呼。通过沉浸在幻想中,他暂时“否认”了自己已是阶下囚的屈辱现实。
四.“否认”为何以及如何形成?
理解了否认是什么之后,往下则更深入探究为何否认会形成以及如何形成。
1.为何形成?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否认”是“自我”为了保护自身完整性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当个体面临的焦虑感过于强烈,以至于有压垮心智的危险时,“自我”就会介入。这种压倒性的焦虑可能源于两个方面:
外部威胁:如突如其来的死亡诊断、毁灭性的失业通知、亲人的背叛等。这些外部事件直接冲击了个体的安全感和存在感。
内部冲突:即“本我”的原始冲动(如我好想涩涩!)与“超我”的道德戒律(如“我要戒色,涩涩是不对的!”)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我”作为心灵的协调者,如果无法通过更成熟的方式(如解决问题、寻求支持)来化解焦虑,就可能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关闭感知的阀门,直接“否认”焦虑源的存在,从而暂时维持内心的和平。
2.如何形成?
现代认知心理学为我们揭示了“否认”在信息处理层面的具体运作方式。它并非一个神秘的过程,而是一系列认知偏差和信息过滤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意力偏差:个体会有选择地避开那些可能引发痛苦的信息源。比如,一个怀疑自己患病的人可能会刻意回避所有与该疾病相关的文章和新闻。
解释偏差:当无法回避负面信息时,个体会将其重新解释为无害的。例如,一个在恋爱关系中遭遇冷暴力的人,可能会将对方的漠视解释为“他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
记忆偏差:对于已经发生的创伤性事件,大脑可能会通过遗忘的方式来“否认”其发生过,这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中尤为常见。
此外,一些普遍的认知偏见也为“否认”的形成提供了温床,例如“证实性偏见”,即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和回忆那些支持自己既有信念的信息;以及“乐观偏见”,即人们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否认”并非一种被动的“视而不见”,而是一种主动的、持续消耗心理能量的现实构建过程。弗洛伊德的动力模型早已暗示,自我需要耗费能量才能将现实挡在意识门外。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维持否认状态可能需要大脑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等情绪中枢进行主动抑制,这是一种活跃的神经活动。那些为自己的否认寻找理由、指责他人、回避话题的行为,都是在积极地维护那个被自己扭曲了的“现实“。这解释了为何长期处于否认状态的人会感到疲惫,也解释了当否认的堤坝最终崩溃时,现实的洪流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
四. 现实中的“否认”:从家庭生活到网络论战
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小明曾是父母的骄傲,成绩优异,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但进入高中后,他的成绩开始下滑,变得沉默寡言,对练习两年半的篮球也提不起兴趣。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师建议他们带小明去看看心理医生,怀疑他有抑郁倾向。
然而,小明的父母对此的反应是典型的“否认”。他们可能会说:“男孩子嘛,到了青春期都这样,过阵子就好了。”或者将原因归咎于外部:“肯定是学校压力太大了,换个环境就好了。”他们拒绝接受“儿子可能心理生病了”这个现实,因为这会严重冲击他们“成功父母”的自我认同。这种否认,让他们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小明的状况也因此可能进一步恶化。在这个家庭系统中,父母的否认像一层密不透风的膜,将外界的帮助和孩子求救的信号都隔绝在外。
再举一个网络现象:“鸵鸟心态”
这个词汇用来形容那些主动回避负面信息、假装问题不存在的行为。在社交媒体时代,这种心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加持。算法构建的“信息茧房”和“回音壁”,使得持特定观点的人可以轻易地屏蔽掉所有相反的证据,只看到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
在过去,一个人的否认需要消耗巨大的心理能量来对抗来自周围世界的不同声音。而在网络上,一个人可以轻易找到成千上万的伙伴,共同构建一个强大的“否认”堡垒。在这个堡垒里,否认不再是个体的防御,而是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任何试图挑战这种否认的外部信息,都会被视为来自“敌对阵营”的攻击,从而被更加坚决地排斥。这使得互联网让原本孤立的个人防御,演变成了坚不可摧的集体幻觉,也解释了为何当今许多网络争端如此两极分化且无法调和——人们捍卫的早已不是事实,而是那个被集体所验证的、用以否认不安现实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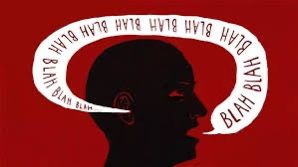
信息茧房的人们
五. 否认一定是错误的吗?
我一直贯彻的理念是,没有任何一种防御机制是错误的,只有“固着”是错误的。当我们固着了“否认”,成为一种长期、僵化的生活方式,它就会阻碍问题的解决、破坏人际关系、扼杀个人成长最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而我们灵活运用“否认”,比如面对亲人的去世,短暂的否认就是在为我们争取接纳现实的时间,维持人格的稳定。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们否认的是不可改变的过去,还是需要我们行动的现在与未来?如果发现自己成瘾于某件坏的事情还在持续否定,这就是在阻碍改变的发生,逃避自己的责任!
六. 将头从沙土抬起,直面真实的自己
我们见证了Y先生的悲剧,小明家庭的悲哀,网络上信息茧房下极端人群的可笑,我们发现,“否认”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心理防御,始终与人类的焦虑和恐惧相伴而行。它愚蠢但是又何其忠诚,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挺身而出,为我们抵挡那些无法承受的真相。
不过,我们无需将其视为一个需要彻底根除的敌人。相反,我们应该学会将它看作一个信号——一个提醒我们内心正在经历巨大风暴的信号。
真正的成长,始于我们将头从沙土中抬起的那一刻。这意味着培养自我觉察的能力,诚实地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想法,分辨我们的“否认”究竟是在提供必要的缓冲,还是在构筑逃避的牢笼。这意味着鼓起勇气,去面对那些我们一直回避的真相,无论是关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关系,还是我们自己。
当然,有些真相过于沉重,我们无法独自承受。这时,向信任的家人、朋友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求助,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可以成为我们重返现实的向导和支撑。或许你可以尝试向一个你完全信任的人,说出一件你一直在回避的小事
最终我们将拥抱现实,即使它不完美,甚至充满痛苦,但唯有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平静、坚韧与自由,甚至连“复仇”也有选择的权利。
如果看到这里觉得还不错不妨点点赞,点点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