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追真者
呂涅與她的未竟遠征
在春意原野瀰漫的血色與絕望中,在堆積成山的遠征隊員遺體前,古斯塔夫顫抖着槍口對準了自己的太陽穴。
準備結束這一切。

在絕望即將吞噬他的那一刻,一個聲音身旁響起,刺破混沌的沉寂。
“你這樣做我們都會死。
難逃一死,又不是現在就得死。
‘有人倒下,也要繼續前行’。”
說這話的人,是呂涅。

重整旗鼓的33號遠征隊艱難探索着,夜間休整的篝火在荒林間噼啪作響。
有人手指無意識地在那把老吉他上滑動,彈奏着無人知曉的旋律。
月光灑在她專注的側臉上,映出一道冷冽的銀邊。
赤着腳的人,是呂涅。

正如她的名字,最早源於拉丁語中的“月亮”,她不是火炬,而是月光。
不是那種會自發光芒的熾熱存在,而是反射着某種遙遠而堅定的光。
清冷、疏離、精確,優雅的注視着地面,爲迷失在黑暗中的人明晰一道可辨的方向。
她以此登場,也以此貫穿始終。
從抽象的知識走向具體的人,從反射的光芒成爲光源本身。
呂涅,一個用理性對抗世界崩解的學者,最終在愛的具體形態中成爲了一個完整的“人”。

一、誕生於遺志的理性造物
在成爲“呂涅”之前,她首先是“知名學者之女”,是“46號遠征隊成員的遺孤”。
她的名字是Lune,“月亮”。
月亮代表的是反射光而非自發光的特質。
她不像瑪埃爾那樣擁有繪師之力的創造力,也不像熙艾爾那樣有着本能的熱情。
這個隱喻從一開始就籠罩着她的人生。
呂涅是盧明一對知名學者夫婦的女兒,童年沒有在遊戲與擁抱中度過的,充斥着數據板和研究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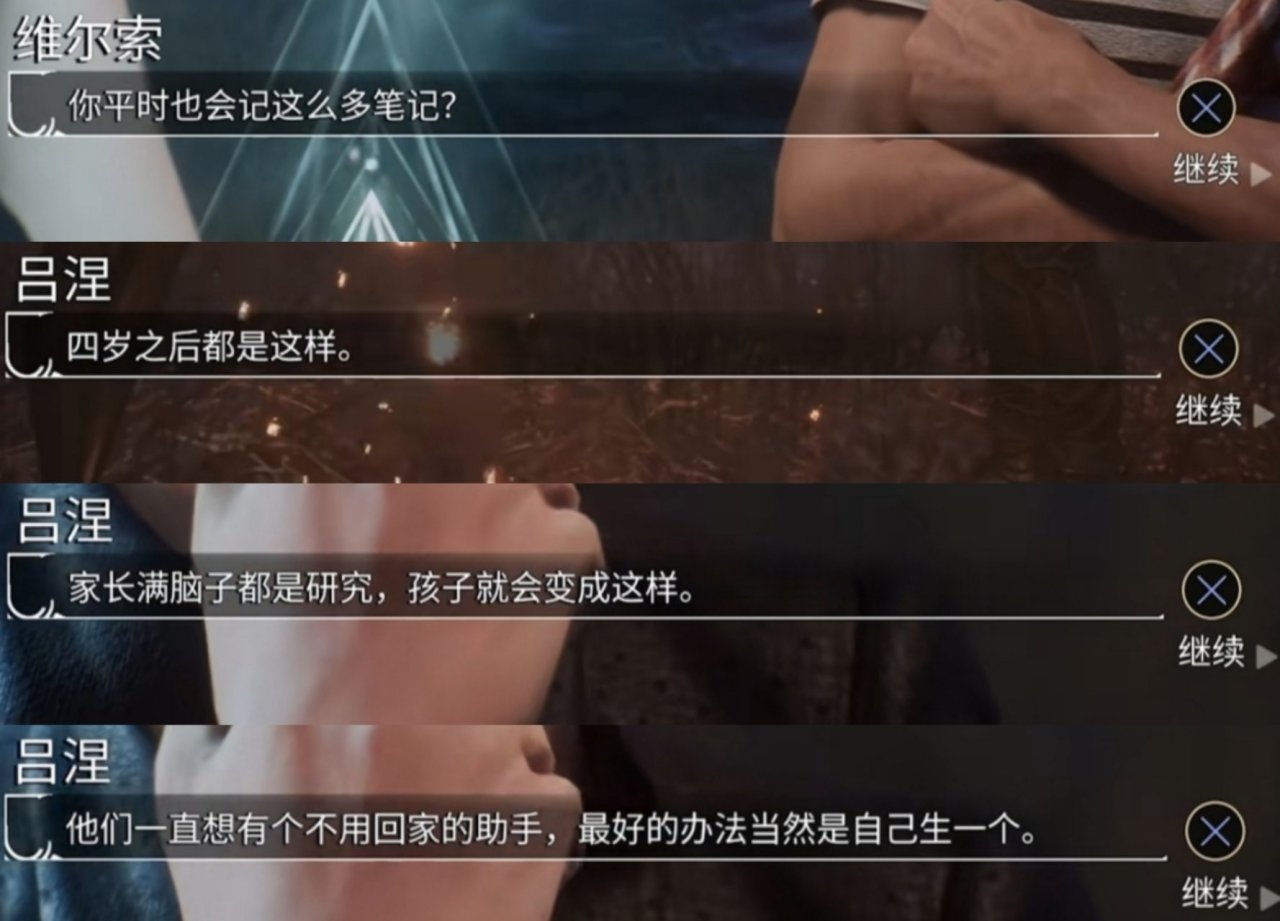
除了一隻名叫“爪爪”的狗狗,家裏還有一個富有活力活得很精彩的姐姐和一個備受家人喜愛的大哥。
那段一個孩童對於世界最初的認識,大概是一間堆滿未完成研究的書房與一個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期望。
所以逐漸長大的呂涅在人羣裏總是那樣冷冷清清的,你能感知到她的優秀,但卻不發着光。
因爲她的光芒來自別處,來自父母未完成的學術研究,來自46號遠征隊遺留的使命,來自她對“真相”這一概念的執着追求。
13年前,她的父母作爲第46號遠征隊成員,在遠征後一如其他隊伍一般未歸。

“他們希望我繼續下去。”
很多個深夜營地,呂涅時常瀏覽父母留下的錄音筆記。
她將自己完全投入到父母的研究中,爲了完成學術使命,爲了在虛無中抓住與父母最後的連接。
這種連接如此脆弱,以至於她長久以來都用絕對的理性來守護。
情感會波動,記憶會褪色,但數據和邏輯永恆。
呂涅剋制着自己,邏輯嚴密,言辭犀利,感性流露會影響效率。
那個渴望父母認可的小女孩,成長爲同輩人裏無可挑剔的領航員和策略家,是“當一個人倒下,我們繼續前進”這句鐵律最堅定的執行者。

這種狀態下的呂涅,活在一種被預先寫就的手稿裏。
她的價值、目標、乃至人生軌跡,早在出生時就被父母的理想所定義。
她追尋“繪母”的真相就只是爲了完成那道被輸入的程序。
二、盧明的年輕學者
呂涅的“毒舌”屬性在遠征隊中是不可少的某種標誌。
我們從序章到古斯塔夫章節的前半段,呂涅展現的,是幾乎算得上刻薄、低情商、偏執的理性。

不斷強調、循蹈那些遠征隊的條律。
對於隊友陷入沮喪、悲痛,露出崩潰情緒時,她會認爲這是不必要的感傷。
總是話語冰冷,甚至鋒利刺人。
要求着團隊朝着她規劃設想裏、標準遠征隊的模樣朝着紀石不停歇的前進。


長期肩負使命壓抑着情感,形成了心理防禦。
每一時刻都需要精確計算,每步行程都應按計劃進行,因爲任何即興發揮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失效。
你不能脫離出她的系統性思考和長遠規劃裏。

三、當理性遭遇具體的人
呂涅這個堅固的邏輯世界,遭遇的第一次劇烈撞擊,來自古斯塔夫。
在兩人從死人堆裏走出來,發現疑似瑪埃爾留下的未署名留言後,兩人的衝突爆發了。
古斯塔夫不顧一切要前去營救,那是他的妹妹,是他無法割捨的情感聯結。
這是一個“具體的人”的邏輯。
我們剛剛着陸人員就幾乎覆滅,那個能躲過抹煞的神祕老頭強大無匹。任務嗎使命嗎紀律嗎,我不知道,去他的,我的妹妹可能還活着,我現在只想找到我16歲的妹妹。

在呂涅看來這是衝動而愚蠢的,所以她嚴斥其不合程序,不合條律。
這條留言根本沒有按規程簽名,真實性存疑,爲一個小概率事件偏離核心任務,更是愚蠢且不負責任的。
此時的她無法理解古斯塔夫那種不計代價的情感,只能用自己任務絕對優先的標尺去衡量,並將其貶低。
那集合點等待三天與永遠不可單獨行動兩條規則,你要違反哪條?古斯塔夫拋出了這個問題離去。

呂涅無法在失去古斯塔夫的情況下獨自完成遠行,反之亦然。
微妙的妥協,是呂涅理性堡壘上破開的第一道的縫隙。
在尋找瑪埃爾的路上,呂涅和自暴自棄崩潰想回老家的古斯塔夫又再次爭執。
“盧明未來”、“任務”、“使命”,這些東西在她心裏從未動搖,她不知道古斯塔夫怎麼了懦弱至此。
因爲“有人倒下,也要繼續前行。”
在爭執和解後兩人再次攜手上路。
此時她隱約能感知到,世間存在無法被邏輯公式計算的價值。
兩人並肩作戰,最終在神祕宅邸找到瑪埃爾。

“是刷頭精!你難道不想去看看是不是真的嗎?”
一隻小刷頭精出現。
這是呂涅一直保持冷靜、理智、思考的臉上第一次出現那麼一個情緒。
興奮的好奇。

完全出自個人心底的情緒。
那可是小時候在童話故事裏聽說的刷頭精欸!他們居然真的存在嗎?!任務?好吧,他們有線索嘛!
三人在刷頭精裏遇到熙艾爾,而後又結識埃斯基耶。
一路相伴中,這個小小的遠征隊,從一個軍事單位,轉變成了一個奇特的家庭。
在這個新生的系統裏,沒有預設的功能性角色。
這是呂涅從未有過的體驗。
在營地的篝火旁,他們分享的不只是戰術,還有童年的記憶、內心的恐懼、脆弱的夢想。
熙艾爾的溫柔包容,瑪埃爾逐漸顯露的堅韌,與沒事扔兩石頭砸繪母的古斯塔夫,共同爲呂涅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安全空間。

在這裏,流露情感不會被視爲無能,脆弱是可以被接納的。
她所激烈抗拒的,自己內心深處同樣渴望卻極力壓抑的那部分。
對個人情感的重視,對具體關係的依賴,悄然浮現出來——
然後。
真正的崩塌緊隨其後。
古斯塔夫在瑪埃爾面前被雷諾阿無情殺死。

在懸崖下的呂涅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時候,她什麼都做不了。
她精心規劃的路線、權衡的風險、冷靜的智謀,在絕對的力量面前都化爲齏粉。
那個溫暖的古斯塔夫死在了她毫無心理準備的瞬間。
古斯塔夫的死,把呂涅的世界砸出了軌道。
三、前行的自我
呂涅最初偏執着,強迫性地要爲“下一支”遠征隊記錄筆記和線索,想退回到她唯一熟悉的那個所謂傳承的框架裏,來填滿失去古斯塔夫的痛苦。
熙艾爾將她打斷。
“不要這麼急,還有明日。”

是的,還有明日,一人倒下,其他人繼續前行。
面對瑪埃爾對自己的斥責,呂涅只是沉默,罕見的別過臉背過身。
“當一個人倒下,我們繼續前進。”這句話倒被熙艾爾說出。
在四人繼續前行被四手劍客擊落墜橋時,瑪埃爾慌張觀望四周,剛站起身的呂涅便趕忙跑至其身前詢問狀況並施術治療。

呂涅逐漸展現出了她理性之外的維度。
她更能理解他人那種源於本能的情緒,開始承認情感因素在決策中的理所應當。
古斯塔夫死後,殘餘的呂涅、瑪埃爾與熙艾爾,在創傷的灰燼中被迫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更緊密的聯結。
哦,還有維爾索。

他喜歡腳?真的?
呂涅舊有的、那個絕對理性的自我正在死去。
她開始變得更像一個“人”,開始慢慢體悟那些曾經不能真正共情的喜怒哀樂。
她也可以是在隊友面前顯露出迷茫和悲傷的呂涅。
這個後天形成的“家庭”,成了一個療愈的熔爐,緩慢融化着她內心的冰層,讓她被壓抑的情感得以浮現和整合。
她第一次意識到,真相的價值。
其實可以不在於它被揭示的那一刻,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同樣寶貴。
人與人之間建立的那些具體而真實的聯結,是真實而溫暖的。

塞壬的幻境,是對呂涅新生自我的一次試煉。
塞壬的歌聲會直擊內心最深切的渴望,爲每個人編織最美的夢境。
瑪埃爾見到了古斯塔夫,熙艾爾與逝去的家人重逢。
而呂涅,自然看到了她的父母。
那個以“完成遺志”爲紐帶的關係。
她從未言說,甚至未曾自覺的渴望,渴望作爲“女兒”被愛,而非作爲“繼承者”被認可。
在經歷了與隊友共度的真實苦難、建立了深刻情感連結的呂涅,意識到,眼前父母帶來的完美慰藉,只是一個美麗的幻影。
接受它,就意味着否定她在遠征途中經歷的一切真實。
那些痛苦、那些失去、那些與隊友相濡以沫的溫暖,都將變得虛無。
她選擇了真實。

掙脫幻象,然後去捍衛那個嶄新、脆弱卻真實的自我。
回到充滿不確定和痛苦的現實,在這裏,纔有她真正愛着、也愛着她的具體的人。
四、在月光背面
在冒險逐漸深入的某夜。
呂涅有些彆扭的詢問維爾索46號遠征隊的情況,用“不便改道”拒絕了維爾索帶她前去的提議。
隊伍還是一同來到了第46號遠征隊海島遺蹟,呂涅彈奏吉他開啓密封大門。
音樂對於呂涅而言,是一種無需數據驗證的表達。
當她的手指在琴絃上滑動時,那些被她壓抑的情感找到了隱祕的出口。
儘管父母認爲那是輕浮的、不務正業的。
她最終找到了46號遠征隊的日誌,看到了母親那句貫穿她生命的遺言。

“呂涅會完成我們開始的工作。”
呂涅一直都明白,一直都是這樣想認爲的。
只是在真的面對父母的死亡,在面對那句遺言時依然有些茫然,有些不知道自己爲什麼要揹負他們的理想了。
她告訴維爾索自己的感受。
“他們沒把我當成女兒,我只是他們的備選方案,唯一的價值是延續他們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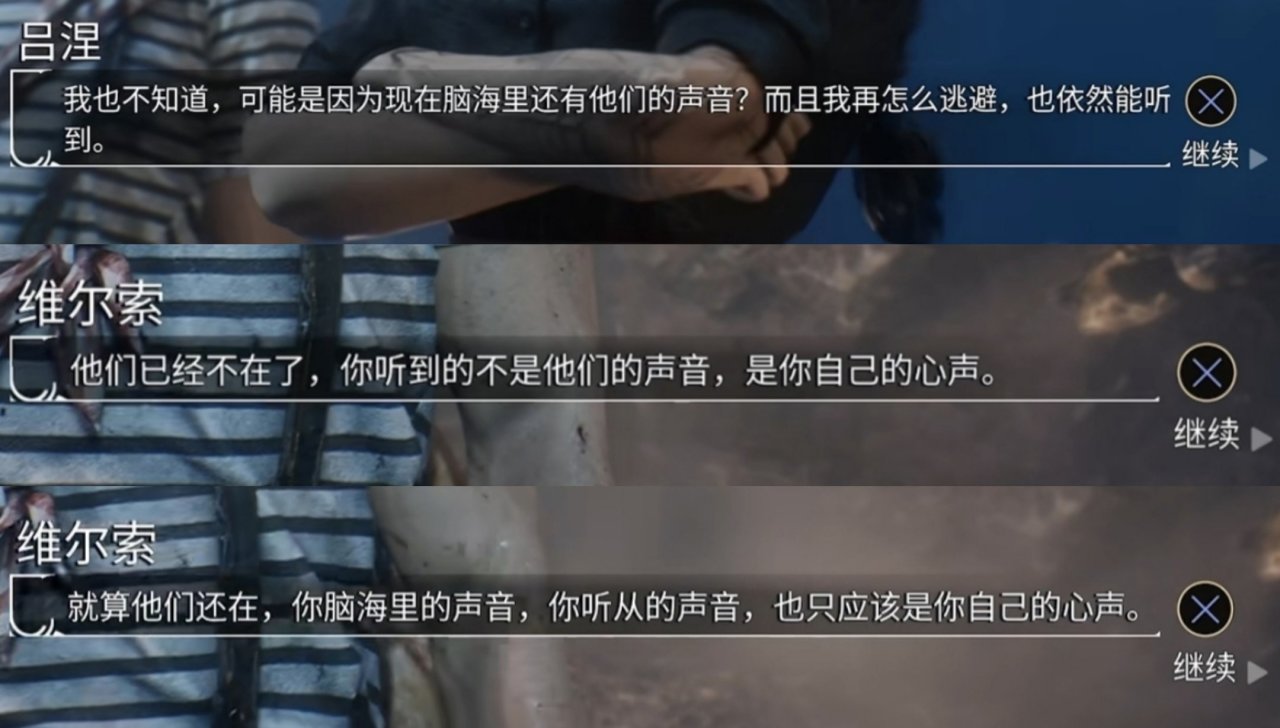
“無論他們是否還在,你所聽到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你應當只聽從自己的聲音。”
呂涅當然是“知名學者之女”,是“46號遠征隊成員的遺孤”,但她首先是“呂涅”。
呂涅的使命感微妙的變化着,完成父母的研究固然重要,理解他們的愛與期望同樣重要。
不是作爲研究者與繼承者,而是作爲女兒與父母。
那就聽從自己的心聲。
呂涅依然前行着,爲了紀念父母,爲了不辜負古斯塔夫的犧牲,爲了保護瑪埃爾、熙艾爾這些她視若珍寶的家人。
作爲一個靈魂完全自由的個體,去用行動向所愛之人做出最深情的回應。
五、未竟

當你耗盡一生去對抗繪母、揭開“抹煞”背後的真相。
卻發現自己身處的整個宇宙,不過是一幅畫。
而這幅畫如今是一個深陷喪子之痛,還死活不肯看心理醫生的家庭大戲場。
紀石之底。
盧明世界不過是現實畫家創造的畫中世界,一切不過是狄桑特家族的愛恨糾葛。
歷經犧牲、懵懂、血戰、勞苦、背叛,被抹煞又被複活。
得知那個令人不知作何感想的“真相”,呂涅和33號遠征隊飽嘗千險走過整個世界,在終於擊殺雷阿諾後,一切又突然結束了。

維爾索最終毀滅畫界。
所以這一切,“我”父母的犧牲,“我們”的遠征,都只是一幅畫裏的情節?
“我”這一輩子,就是給人家庭矛盾當背景板?
呂涅是唯一沒有與維爾索互動的角色,就這樣獨自癱坐。
眼神中沒有崩潰,只有不甘、憤怒與拒絕。
“即使我們是畫中人,我們的情感、記憶、追求就是虛假的嗎?”
她不會接受。

『月亮的歸途』
在遊戲的最終,呂涅依然是個複雜的存在。
她理性,但不冷漠。她毒舌,但不刻薄。她執拗,但學會了相讓。
追求真相的學者,終於明白有些比真相更重要的東西,藏在追尋真相的路上。
“當一個人倒下,我們繼續前進。”
那時的她,以爲“繼續前進”意味着揹負逝者的遺志,替他們完成未竟之事。
到遠征的盡頭時,她已經瞭然。
繼續前進,是帶着他們給予你的愛,活成你自己想要成爲的模樣。

呂涅依然完成了一場屬於自己的遠征。
她不再是那個只爲完成父母遺願而活的學者,她成爲了她自己選擇的領航者。
她完成了從反射他人光芒到自身成爲光源的質變,像月光穿越億萬公里宇宙。
愛不是空洞的理念。
愛發生在具體的人之間,發生在共同的傷痕與篝火旁,發生在每一次明知危險卻依然向同伴伸出的手中。
她的“用一生去愛”,愛的不是遙不可及的真理幻象,而是此刻並肩而立、有血有肉的靈魂。

那些被她反射的光,在她體內沉澱、交融、淬鍊,化成了獨屬於她自己的、名爲“呂涅”的輝光。
月光清冷着,卻輝映夜行人的路。
它灑向的不只是終極的答案,
更投射出那永恆明亮的歸處。
這一輪幽月,終於爲自己,
照亮了來路,也照亮了歸途。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