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在廣場邊上看到兩個騎單車的小學生,一男一女,校服被風鼓得滿滿當當。就在經過我面前時,那個男生突然把雙手從車把上撒開,故作輕鬆地插進口袋——或許是想在小女孩面前耍帥,或許只是“雙手插兜,不知道什麼是對手。”
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童年,和通遼狠人達爾一樣潦草地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大撒把。那時村口有個巨大的土坑,像是乾涸多年的湖牀,邊緣被歲月磨成緩坡。
每天下午放學路過的時候,我總會騎上那輛老舊的自行車,在坡頂深吸一口氣,然後不扶車把的從坡上呼嘯而下,讓風吹過自己耳旁,心隨着大槓飛揚。只要想到這種與“投胎”無限接近的感覺,就會幸福地全身發抖。那種感覺就像是楚雨蕁喫花椒,“爽”麻了。

是什麼時候不再這樣做的呢?記憶在這裏變得模糊。也許是因爲後來土坑被填平,蓋起了新房?也許是因爲某一次,車輪壓到坑窪顛簸中失控,連人帶車摔進坑底的乾土裏,膝蓋和手肘火辣地疼,血混着泥土凝成暗紅色的痂。
檢查了一下車子,幸運的是——車,安然無恙!比起疼,當然更怕的是回家捱罵。於是我拍拍土,扶起車,果斷的在A或B中選擇了“或”——再玩一次。(衣角微髒而已~)
那一次,大概就是最後一次。
如今回想,那樣純粹(傻),早已被歲月悄悄收走。以現在的眼光看,這種極限運動,除非紅牛贊助,我大概是不會再嘗試了。有時候也會想,早知道長大這麼累,當年摔在溝裏時,不如就躺在那裏,多躺一會兒。
後來,大學實習那會,我給自己換了個安全的愛好——長跑。每天下了班,跑會兒小步,多是一件美事。而每次快要跑完十公里時,最後幾百米憋着一口氣衝出去。心率直逼兩百,山風從耳旁呼嘯而過,那種熟悉的、屬於風的自由,讓我在奔跑中重新找到了大撒把般的快樂。
那時常去一條僻靜的村道夜跑,準確來說,是廣西鄉下山間的夜路。路上的行人,不能說是人山人海吧,也只能說是幾乎沒有。只有路燈把自己的影子拉長又縮短,世界縮成眼前一道向前延伸的光暈。彷彿不是在用腳跑,是夜色在用我,推開它自己。
漸漸地,在這份自失的背面,卻浮起一絲極淡的、揮之不去的異樣感,太靜了。
後來我有點疑惑:路的左邊是座小學,按理說也不至於這麼清靜。正想着,瞥見道旁有處不起眼的石階,通往稍高一點的土坡。靈機一動,便站了上去。事實無數次向人們證明,人有時候還是不要“靈機一動”的好。
然後我就看見了,那座山的整個向陽坡,是一片安靜的老墓地。石碑在夕陽下泛着溫暾的光,挨挨擠擠,又整整齊齊。
我站在石階上愣了一會兒,下來後,我係緊鞋帶,重新跑了起來。自此,每次從那裏路過,心裏便默唸:“我是路過,純路過,真的就是路過……”偶爾能聽到左邊的小學下課的場景,嬉戲打鬧聲像一種溫暖的背景音,聽見這聲音,心裏那點發毛的念頭便消退了,優勢在我。

跑步好是好,只是有個小問題:廣西經常下雨,當然在細雨中跑也很爽就是啦。可天氣太冷一跑完就容易小感冒,在廣西這樣溫吞的地方都這樣,別處就更不必說了。
後來索性認了,只當它是份屬於秋天的特權。於是每年風起時,我才把自己還給自己,就像那個被填平的坑,就像那陣掠過耳畔、不再回來的風。
我總在相似的呼嘯中,找尋着相似的自由。
再後來,我去了中國最西端的帕米爾高原。站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西風浩蕩而來,毫無阻擋地穿過我。那一瞬間,我忽然想變成一隻“狗”(最好是隻薩摩耶)在這鮮花芬芳的西風盡頭——追着風的尾巴撒歡,一直跑到西風的盡頭去。
風永遠不會被追上,就像人永遠無法真正變成一隻撒歡的狗。那一刻極致的嚮往與註定無法抵達的悵然,讓我想起了那個關於海鷗與薯條的段子。


“想去碼頭整點薯條”,大家都羨慕那隻海鷗,嚮往那種不顧一切的颯爽。但說到底,絕大多數人終究還是那根薯條。
我也常看那些活得張揚鮮亮的視頻,羨慕他們彷彿掙脫了所有繩索。或許鏡頭之外才是生活笨重的底色。所看見的精彩,不過是他人願意讓你看見的片段。普通人就算真去“整了薯條”,做完這一切,大概率還是會拍拍灰塵,轉身走回原來的軌道,上學、上班、生活照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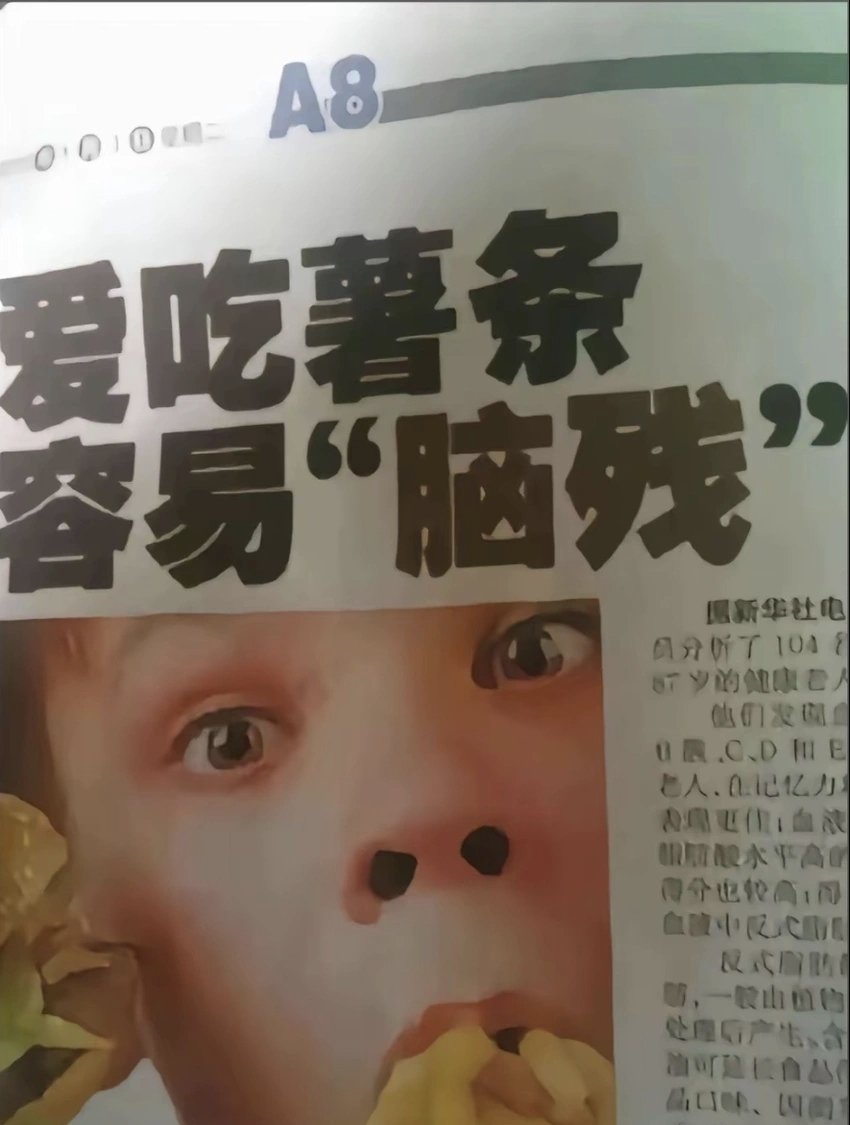
因爲做喜歡的事,往往需要付出代價。或許論文全未寫,或許考勤已記缺。或許存款全清零,或許工位已除名。可人就是這麼奇怪,明明知道代價,所有理智的警告都攔不住心底那句“非做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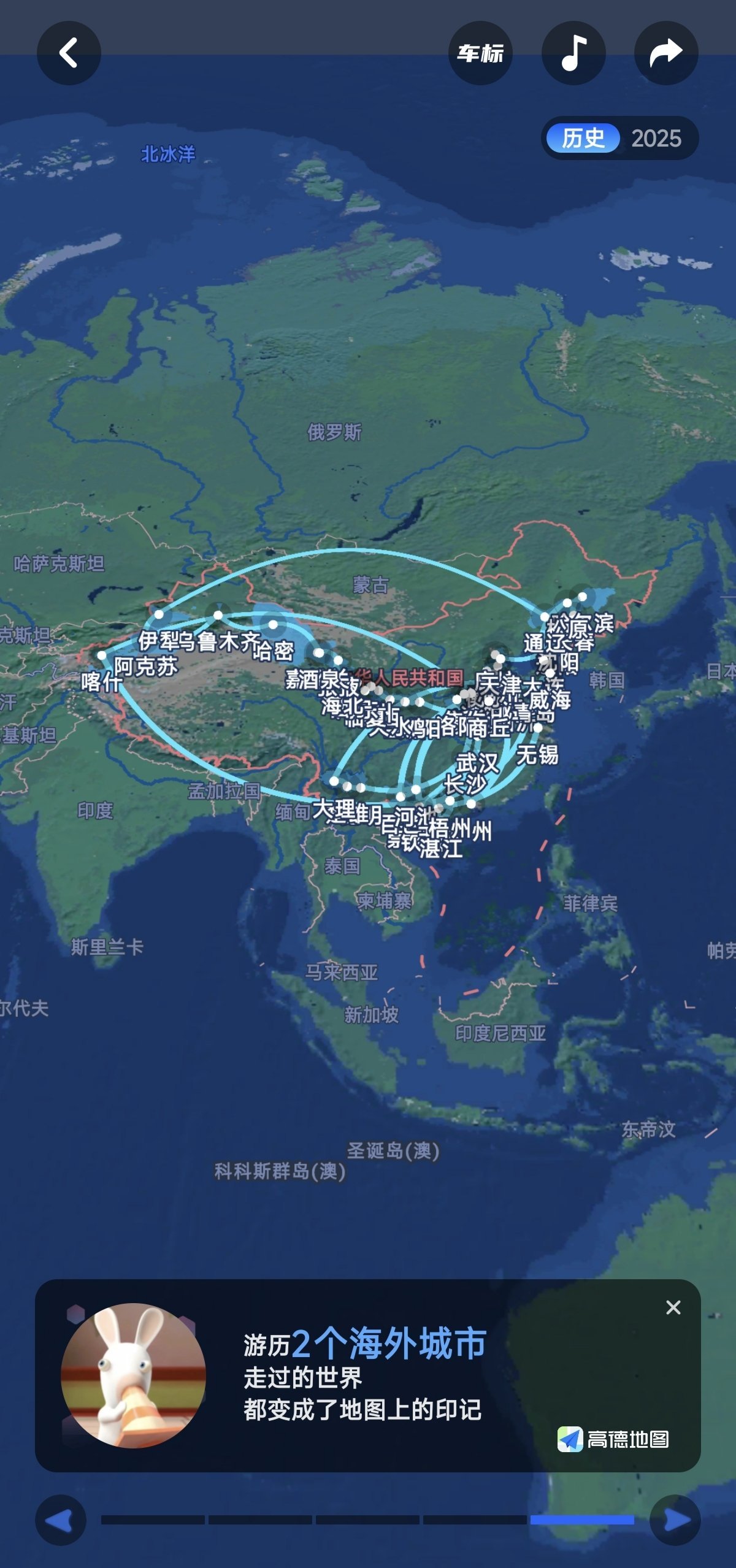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或許,那種本能從未真正離開。
它只是從童年飛馳的土坡,躲進了秋天鄉間的跑道,又藏在了高原劈面的風裏,我依然能感受到零星的自由。而我一生所最終追尋的,不過是那個坐在自行車上、衝下山坡的下午。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考完試了你才交焚決是吧[cube_生氣]一週速通教資考試指南,進來插眼!](https://imgheybox1.max-c.com/bbs/2026/03/07/3c46adc40661c956458504af1dfb765c.jpeg?imageMogr2/auto-orient/ignore-error/1/format/jpg/thumbnail/398x679%3E)

![慢訊:阿里通義千問Qwen核心負責人離職[cube_滑稽]](https://imgheybox1.max-c.com/bbs/2026/03/07/381409aa8b7b37bd877f9706e0a22f64.jpeg?imageMogr2/auto-orient/ignore-error/1/format/jpg/thumbnail/398x679%3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