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天我手机摔坏了屏幕,所以换旧手机用了两天,手机卡顿得我都不想用了,因此这两天手机的使用时长是我有意识控制以来这两个星期里最低的。
也正是这段时间我意识到我现在的注意力大不如前了,人也懒了很多。我现在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每次看完一本书就要马上抽时间去写上一篇读书报告。
直到我出现对信息洪流的厌倦开始增多,直到我意识到我多数时候都是无意识的做着流水线一样的习惯性动作。

“手机倦怠”
我还不自觉的掏出手机,解锁手机,然后随机打开一个常用的应用,视频平台或者游戏论坛,甚至购物软件。有些时候,不知道干什么也会掏出手机,解锁手机滑动一下屏幕,然后又放回去。
一时间,我也分不清我是真的需要如此频繁的使用手机,还是我的思绪在长年累月的手机使用上产生了习惯性的依赖?我相信我是后者的概论更大些。
这种依赖在心理上表现为我不想空耗我的每一分钟,所以在之前上班的时候,即使我不能像现在这般肆无忌惮的刷视频,我依旧会有很长的手机使用时间。我会在工作不紧急的时候听上一整天播客,却很少会听一整天音乐,一是因为觉得音乐是“无效率”的,即不会给我任何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播客会有一种交互感,好像坐在交谈者的对话局里,好似多了一分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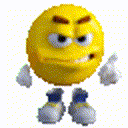
效率不是一切
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起,有了如此强烈的效率意识。可能是在小学学习“同步安排时间表”时,领略过效率高的样子开始,我对效率产生了误读。导致我在后来的这么多年里都认为“有效率 = 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但事实上,人的大脑对于信息的处理是极其有限的,相当的情况下都是习惯于只处理一件事情。
加之在我多年的受教育经历里,都是传播着“活到老,学到老”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当然这种持续性学习和发展的理念没有什么问题。似乎只有不断地摄入信息,不断的学习才是“正确的”,这也让我再某种程度上害怕落伍,害怕“没跟上时代”。
当下的互联网语境和时兴的事物都是迭代极快的,我们很难做到绝对能够一字不落的跟上步伐。可我们真的需要都记得吗,那你还记得十年前最热门的话题和梗吗?
约翰.伊斯特伍德在解构现代人群的信息焦虑时,说到如今人处于一种难以忍受的隐约且漫长的无聊,好似感染了一种“无聊传染病”。由于精神刺激太多,意义却很少,因而留下的最终还是无聊。处理摄入的信息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同时我们的信息累积是如此之快,而意义的创造却是无比缓慢的。因而在过量的信息灌入大脑之后,好像得了“慢性信息消化不良”,只会留下一阵空虚和落寞。然后照旧拿起手机去安抚这种懊悔情绪。

《我们为什么无聊》书摘
此外,现如今的社会生产与生活逐渐被模糊了边界,人的劳动也被模糊成了不同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注意力资源。上班时,是提供劳动力价值,下班后的时间里,提供的是注意力价值。
当代人的娱乐方式不同于过去互联网与移动设备没兴起之前的情况,过往的劳动生产是与生活直接分割开的,下班之后的生活方式就是直接离开再生产的,而当下的人们即使下班了也会再次各种流媒体、视频平台当做再生产的劳动力,被量化成了注意力资源,甚至重塑了一种不自觉的消费习惯和滋生了一种潜在的消费冲动。
在我近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测试里,我留意到我的这种无意识刷手机的冲动正在处于一种“燃尽”状态,我已经开始对刷手机这件事本身开始有了倦怠。
而我逐渐开始用其他的“动作”去替代刷手机的这种下意识状态。用学习一些技能的动机去视频平台有意识的看视频,而非漫无目的的刷视频。用写杂感和思考短文的方式去替代过度刷论坛帖子。似乎在这些慢动作之后,我也没有脱离“时代发展”的脚步,而信息焦虑和无聊也被逐渐消解。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