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在退场,有人在等位。
我知道你,你是一个漕河泾的游戏打工人。
徐汇漕河泾,占地近五平方千米,地图上标明的、未标明的、大大小小的游戏公司数不胜数。这里诞生过《原神》这样的爆款,也出过无数换皮小游戏,而你就身处其中一家公司。

你是9号线、12号线百万通勤者中的一员,每天早高峰随人流从4号口、7号口涌出地面,踏上前往工位的固定路线。配表、跑检查流程、和同事扯皮——这就是你的一天。
公司规定晚上七点下班,但最近项目在赶暑期档活动,手头的活还没做完,新需求又一波接一波,你常常加班到夜里十点,好在十点之后打车可以报销。
晚上十点的漕河泾依旧堵车,沿路的游戏公司还亮着灯。接单的司机师傅热情洋溢,盛赞写字楼里的都是科技人才,手握高薪,创作“第九艺术”。你迷迷糊糊地强撑着眼皮点点头,一边与有荣焉,一边又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师傅夸的那种人才。
好不容易拖着残血状态回到那个每月吞掉你三分之一工资的落脚点,洗澡、睡觉,缓慢回血。你闭上眼,准备读档重启,任务栏还在梦里闪烁——欢迎回到“土拨鼠之日”,一个永不掉落通关奖励的无限副本。
当然,这也未必就是你。在漕河泾打工的游戏人千千万万,众生各异。就算粗浅划分,也大致能划出三类人:准备进入这个行业的;已经在这儿打拼了不短时间的;还有那些,正酝酿离开的。
我问他们,漕河泾是什么?
有人说了三个字:食住行。没错,漕河泾打工人并不在意“衣”,带着大logo的公司文化衫即穿搭精髓。
也有人说了四个字——应许之地。但应许的,是哪一片土地?哪一个时刻?又是许给谁的?没人能说得清。

“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
莉莉丝和米哈游的班车每天早上会经过桂林路的十字路口,顺着人流往宜山路方向开,出现概率不低,像是游戏里定点儿刷新的背景板。

大胖每天等红绿灯时,偶尔能瞥见它们从身边掠过。他听说那只是从地铁站开到园区的接驳车,真正的通勤路程还得靠双脚补完。但那一刻,贴着“米哈游专用”的车厢看上去依然像是某种遥不可及的“传送门”。
他自己在漕河泾一家没有班车的小厂做QA,住得不近,但好在地铁直达,不用换乘。一个小时的单程通勤,换来更低的房租和“少折腾”,他觉得还行。
QA的一天,从和策划斗智斗勇开始。作为“策划——程序——测试”路径的最后一环,大胖负责测试新版本内容,确保“新胚子”的效果和数值都符合预期。策划和程序的环节有什么变动,他这里都得跟着调整,所以每天上班免不了和策划battle。
而且,公司还在搞“出海”,不同国家和地区要适配不同版本和上线节奏。各地的DDL像连发的弹幕一样乱入他的日程表:上午刚交完A区1.0的测试,下午就得拉会准备B区1.1版本。面对这种气都没空儿喘的日常,大胖也只能自嘲一句,“很充实”。
每天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着他赶任务。公司偶尔群发几封邮件,尤其在年中和年底,总在讲战略、谈愿景、提增长。大胖点进去看一眼,又默默关掉——反正也和他没啥关系。
刚开始上班时,大胖还是一个热血少年,现在每早打开电脑,他只会在心里默默弹出一个问号:“让我看看这群聪明的策划又搞了什么幺蛾子?”
几年干下来,大胖只有一个感受:难顶。“现在的项目周期变短,人员变动也大。除了每个版本的胚子外,还在加玩法养成维度等各种功能,人少、时间短、耦合多,节奏挺紧张的。往往当前版本还没搞完,就要开始准备下个版本了。”
而这一切,其实和大胖最初对游戏行业的想象差距不小。当时,一位已身处“毒圈”的朋友一句“快来,这里钱多事少能玩游戏”,把他忽悠了过来。他信了,也动了真格,带着一腔热血决定大干一场。

彼时,大胖在的公司正全力开发一款卡牌游戏,对标的是友商一款长期霸榜的爆款。抱着跟它“掰掰手腕”的决心,公司卯足了劲儿招人开发,底下的员工也连轴加班。项目上线前一个月,大胖每天都能吃满十点以后打车报销的“福利”,周末双休也变单休、甚至无休。
终于,项目上线了,但成绩却没达到上层预期。项目组的人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裁员通知就接踵而至。大胖当时惴惴不安,悄悄开始物色新东家,经历过卡牌项目上线即裁员的戏码后,他决定换个赛道再出发。
当时二次元游戏这个赛道正火,以米哈游为首的二游厂商风头无两,上海“四小龙”初成气候,腾讯、网易这样的大厂也在到处投资初创团队和公司,市场上频频传来二游立项的消息。

米哈游大楼,图源网络
大胖也想借机转赛道,但过程却一波三折。他没有二次元项目经验,对看中垂直赛道经验的游戏厂商来说,并不是最佳人选。不过,比起从0开始的行业新人,大胖还有一点优势——有上线项目经验傍身,这让他进入了几家二游厂商的面试环节,其中,成功几率最高的是库洛。
“当时我已经进三面了,”大胖现在讲起来还是有点儿惋惜,“最后还是因为项目经验不对口被刷了。”
也说不清算是幸运还是不幸,大胖骑驴找马的面试历程虽然不太顺利,但最终公司的裁员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只是,风浪稍歇后,他那点雄心壮志已被磨得七零八落。
“降本增效”的风吹过去以后,有人潇洒换行,有人暂时蛰伏,这股风如今还没停下,被吹倒的,也还没站起来。
大胖讲这些时没什么情绪,只淡淡地说了句:“后来就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到现在已经觉得,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了。”

离开米哈游,她成了COS裁缝
龙妈之前在米哈游工作,去年12月初,龙妈被HR叫过去,对方说了一大堆,但她听明白了核心意思:可以签协议走人了。
她并不意外。龙妈所在的平台组,不挂靠具体项目,早在那次谈话之前,组内气氛就已经山雨欲来:会上被批评的次数多了,新一年的预算领导没着急让做了,大家都心照不宣。真的轮到自己时,反而有种“终于轮到我”的释然。
老东家的待遇在业界出了名的好,离开时她并不愤懑,自觉拿到的也算值回票价。那天和HR聊完,龙妈径直跑去东华大学,报了高级服装设计精修课程。也是天意,她报的这门课正好下周一开学,时间卡得刚刚好。
“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龙妈说。她本身就是个喜欢COS的二次元,每次去漫展,都听coser朋友抱怨好裁缝太难找,“所以我之前一直想,要是哪天不在米哈游干了,我就去学怎么当裁缝,然后,真被开了,那我就去呗。”
第二周周一,龙妈已经坐在学校的缝纫机前了。最开始的课是缝纫工艺:怎么踩缝纫机,怎么走直线、踩圆弧。枯燥,却是必须得练的基本功。

“我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缝纫机不会跟你扯皮,练得足够多就一定能收到正反馈。”她说。之前在公司,为了推进工作,每天80%的时间都花在了沟通协调上,常常一言不合就想拍桌子吵架,“但是做衣服的时候,就会感觉,世界真安静啊。”
这门课今年六月结业,龙妈打算当个二次元裁缝,帮人做做COS服,跑跑漫展。她不是没想过再找工作,只是今年的就业形势——相信不用多说。
“降本增效”这四个字,到了2025年还在追着人跑。市面上仍在招聘的游戏公司,似乎不缺管理层,也不缺正职,只缺愿意在管理层手下做事的人和“外包”。
她也思考过,游戏行业究竟在变成什么样。龙妈比较认同蔡浩宇之前发表过的暴论:未来游戏行业只会有两种开发者,前0.0001%的天才带领精英团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以及99%的业余爱好者开发满足自己想法的游戏。至于从普通到专业的游戏开发者,蔡浩宇建议考虑转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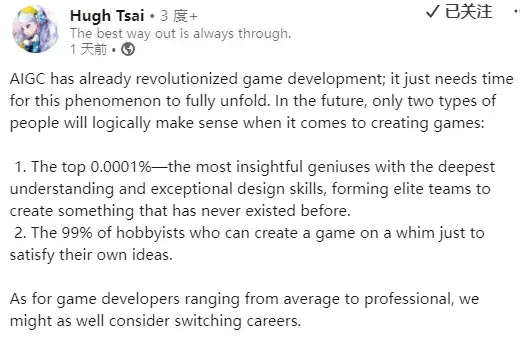
AI对行业的冲击,远不止于催生一波“XXlike”产品的风潮,而是对整个商业逻辑的重塑。
整个游戏行业迭代不出新的玩法,只能不断“缝缝补补”。你能看到大世界言必称“捉宠”、“二次元GTA”,生活模拟迭代好几年还是绕不开“动森”的循环套娃。在这种停滞中,AI成了新玩法的“平替”:AI原生驱动、AI NPC对话......厂商们押注AI,不仅为了降本增效,还期望它能带来一点真正耳目一新的突破。
当下,游戏圈三大基础品类——枪、车、球,轮番被AIGC“洗”了一遍。我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游戏厂商开始推出虚拟人,甚至接入大模型,让人机对战的体验逼近物理世界的真实感。AINPC在聊天中插科打诨,有时真的会让人捧腹大笑。

前文中提及捉宠大世界、类GTA等产品,也得益于AIGC的加持,角色、场景建模生产周期从原本的季度、月度压缩到如今的周更,产能高到不可思议。
假如游戏厂商无法创造出好玩的新玩法新机制,那就只能在横向上堆料,把成功的那一套再拆开重组一遍,让玩家以为这个世界还有无限可能。加入AI后,所谓的个性化体验指数级上升,不过这种情况也只是掩盖玩法老套的一层皮肤。
当然,好故事也能成就一款好游戏,但写出一个能跨越文化、稳定输出、打动多数人的“好故事”,难度不亚于创新玩法。
AI写不了好故事,但它能较好地满足玩家想要的千人千面体验,甚至做得更好——更精准、更快、不喊累。当AI在游戏玩法上的应用真的达到、或者即将到达这一步,那99%的人工,其实也就不再必要了。
“这么说挺残忍的,但事实就是这样。”龙妈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注定有一天要被AI取代,那不如就去做点我喜欢的事,做点AI做不了的事,比如踩缝纫机。”

理想太满 简历太轻
想进游戏行业的小黑,在我看来,有点儿像刚来上海的大胖,也像入职米哈游前的龙妈。
跟龙妈一样,他大学毕业就进了一家知名大厂,不是游戏公司,但也赫赫有名。结果工作不到一年就赶上整体裁员。
他对游戏行业的期望,和当年大胖的想法差不多:钱多、能打游戏。倒也不指望“事少”,他说:“我也没什么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一定要分开的想法。甚至有时候出门没带电脑,我会有点不安。”
去年,小黑从上海去杭州CP展玩,随身带了两台电脑——一台工作用商务本,一台自用。他说因为他还有些物料要赶,而能让他这么敬业的前提是,公司得给够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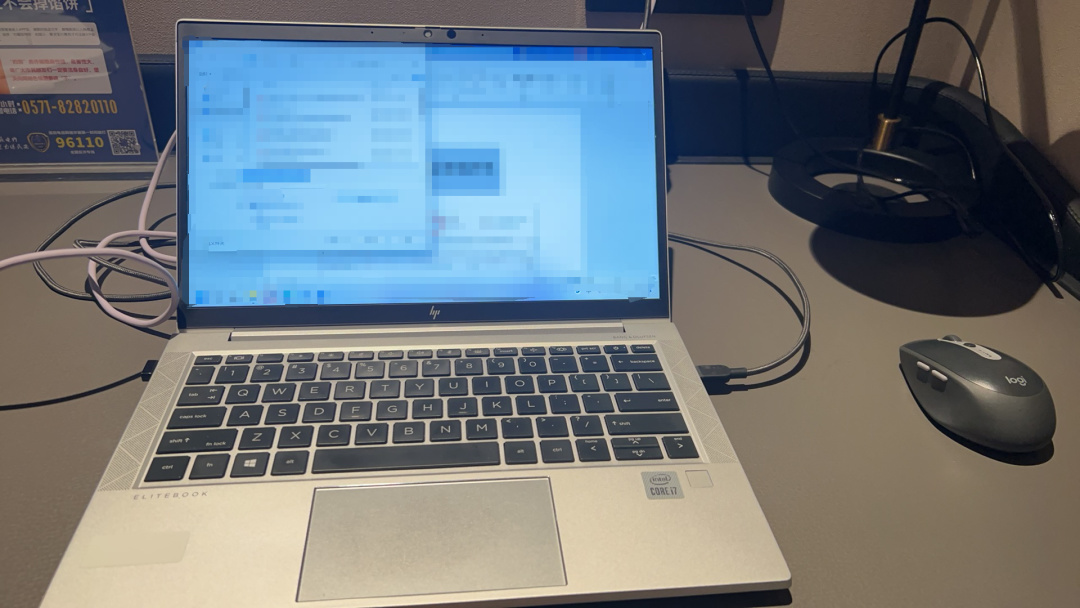
小黑在杭州的酒店里干活
行业内外的人看游戏行业,确实会有些不同看法。小黑觉得,相比他之前接触的电商行业,游戏行业(非单个游戏公司)其实更稳定。
小黑之前做市场营销。他说,电商现在太卷了,一个新热点出来,之前做的一切就轰然倒塌,现在的大环境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人总归是要娱乐的,娱乐就会有游戏,所以他觉得游戏行业本质上更稳。
但在漕河泾游戏公司待过的人或许不这么想。龙妈觉得,不止上海,整个游戏行业都在“刷新”。人员流动快、外包岗增多,转正HC越来越少。
买量也在缩减。根据Dataeye数据,2025上半年,手游APP买投放素材量仅约1580万,对比去年同期下滑近25%。同时,今年新增投放素材也创下三年新低,重复利用成了常态,新增投放游戏数也创下新低。
小黑想去游戏公司市场买量岗,现在已经投出了五十多份简历,数量不多不少。但他说每一份都认真修改了内容,确保和岗位匹配。只要觉得自己胜任不了,他就不会投。
但结果呢?零面试。
最常见的拒信套路无非是:“感谢您投递XX岗位,经过谨慎评估,您与此岗位匹配度较低,期待下次有机会与您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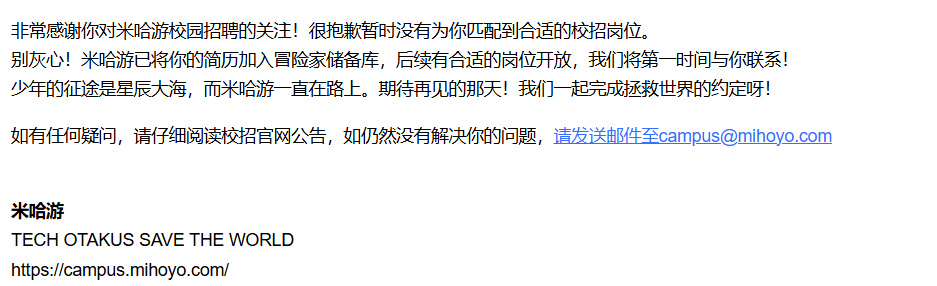
能收到拒信还算好的,更多的情况是简历发出去杳无音讯,被泡在简历池里不见天日。小黑其实有点泄气,有好几次,他眼睁睁看着对面HR已读不回,想问一句“我到底哪里不合适”,却没人搭理。他开始怀疑方向,整个人像卡在了一个流程出错的游戏副本里,无处提交 bug。
这种“找不到入口”的状态,不只属于无经验的新人。整个游戏行业僧多粥少,一个待遇合理的岗位有无数候选人,行外人想被选上难如登天,业内人想要转岗、换赛道也难以找到突破点。
上面提到的大胖是这样,去年通过校招进入腾讯游戏的影子也是这样。
影子的专业是关卡设计,目标岗位自然也是关卡策划,可最终收到的,却是一份与她期望不符的系统策划offer。
在大厂的招聘流程里,校招生其实没什么话语权。影子能做的就只是不停投递,然后等待——等待被某个项目组的面试官捞起来,等待七个小时时差下面试会议的开始。

漕河泾枫林国际科创园
“作为求职者,我没有办法轻易对任何一个机会说No,更何况那可是鹅厂。当我面前只有这份系统策划的offer时,即便和我的第一志愿不符,我肯定还是选择接受。”
进入腾讯游戏的一年里,影子尝试过寻找转岗机会,却囿于没有垂直经验,多次碰壁。转岗不顺之外,学生到职场人的身份转变也一度让她很难适应。
在学校时,作为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影子更注重自我表达,期待游戏创意能被完整落地。不过进入职场后,作为鹅厂游戏的策划,她在设计一项功能时,必须优先考虑玩家偏好,以及是否有数据能支撑这项功能证明存在的合理性。
能校招进入鹅厂的影子,其实已经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大多数时候,她都能坚定地朝着心中的热爱迈进。但偶尔,当发现对职业路径和工作内容几乎没什么选择权时,她也会感到些许迷茫。

靠热爱能否冲破围墙
到这里,似乎可以说,游戏行业是一座围城。
城里的人要出去,城外的人要进来,打工人总在城内城外反复横跳,从一个围城换到另一个,从大围城跳进小围城。
但要说所有游戏打工人都困守围城,也不尽然。在这座被称作“第九艺术”的殿堂里,依然有不少因热爱而自得其乐的人。

漕河泾光启园
就职于游戏外企的小白就是这样的人。他很纯粹,毕业求职时发现只有在面游戏公司时,自己才是快乐的,就毅然决然投身游戏行业,哪怕之前的实习经验并不“对口”,因此贬值也在所不惜。
刚入职时,小白是以玩家视角来做项目的,结果很快就被现实打了当头一棒。公司更愿意在商业化设计而非玩法上下功夫,项目组有的同事和领导甚至都不怎么玩游戏。“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做游戏的怎么能不玩游戏呢?”
经历过时间的捶打,小白现在已经能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些了。项目为了活下去,做一些妥协和平衡,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除了这些必要的让步,他对游戏行业的热爱和坚守四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他痛快承认,自己之所以能保持热爱,离不开一个好项目和一个好公司。
一方面,他现在就职的这家外企游戏公司,真的会把玩家当回事,这与他的理念不谋而合;另一方面,公司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自由度和试验空间。
“我们公司内部会有一些孵化项目,都是员工自己的提案,提案过了,公司就给你配点人去推进这个项目,或者你自己找些朋友一起来做也是允许的。”小白对公司这项制度赞不绝口,“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愿意待在这家公司的原因,我期望游戏行业能带给我的,就是不断学习、不断解决问题的机会和快乐。”
当然,小白也知道,自己算比较幸运的那一撮人,他无意用自己的经历反驳同行们正在经历的痛苦和迷茫。
毕竟,游戏行业确实存在一些令人无奈的现象,这座围城的墙变得越来越高,不只是招聘标准水涨船高,行业内转岗、换赛道的壁垒也在强化。
网上有人打趣:现在游戏行业对垂直经验的要求之严格,就相当于,你只要在肯德基炸过鸡块,就应聘不上麦当劳的炸薯条工作,因为麦当劳只要之前炸过且只炸过薯条的。否则 HR 会追问:“你为什么还炸过鸡块,是不是职业规划不清晰?”
听着夸张,但我的一位想从社区运营转岗系统策划的朋友,前阵子在面试中,真的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采访的最后,我问那些在围城里徘徊的人:“漕河泾,或者说游戏行业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小黑的第一反应是“莉莉丝”。因为这家公司的大巴固定停在科技绿洲附近,他之前来漕河泾出外勤时总能看到,印象很深刻。离职后,他也向莉莉丝投了简历。可惜——从来没有收到回复。

现在,小黑主观上仍然渴望进入游戏行业,但客观上,他已经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登上那辆游戏行业的大巴。
大胖说,他不是没感觉到游戏行业这阵子的热火朝天。版号如热浪袭来,新游戏一波接一波,他自己在玩的游戏也开了暑期档活动。
但这热闹似乎也和他无关——火是游戏的火,加班是自己的加班。他常常还没来得及体验玩家视角,就已经被堆叠如山的任务压成了“测试怪”。
影子则想起了她所崇拜的一位女制作人在半年前分享给她的话:
“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学到游戏设计的知识,只要你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事,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停下脚步,不断前进。”
“坚定地前进是前进,迷茫地前进也是前进,只要继续走,就一定会看到更多路的。”
(受访者均为化名,为保护隐私,部分信息做模糊处理)
更多游戏资讯请关注:电玩帮游戏资讯专区
电玩帮图文攻略 www.vgov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