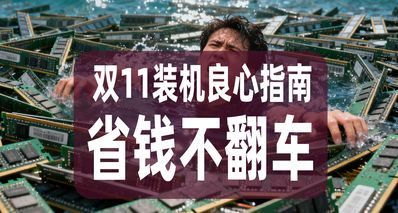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
不久前,“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還沒有被陳詞濫調的嘲諷,“內卷”的行爲也有那麼惹人眼球,即使填鴨式的教育嚴苛不已,人們也依然相信學習是唯一的出路。
如今,信息時代的高速發展將不同階級的民衆都集結到了一起,個體與集體間衝突被無限放大,很多人都會對網絡上具有熱度的人各抒己見,自然一些 豐功偉績的人物也逃不過網民不顧是非的審判。
張桂梅校長便是被聲討的其中之一。

即使她曾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女子高中,帶領被時代“遺棄”的女孩走出大山,即使她曾以一己之力對抗無形的父權制度,在多方言論的壓力下矢志不渝,即使她身患重病、一貧如洗,卻還堅持不懈的守在崗位上拯救“下一代人”,這一代的人卻依舊在無情的質疑。
但網民之間的對錯本就無法影響張桂梅校長的行爲正當性,形象或被污衊,“本爲高山,蔑視懦夫”的人生卻永遠無法抹去,我便寫下這篇傳記,歌頌她神性的“捨生取義”,人性的“理想主義”,以及dang性的“信仰篇章”。


——你好,張桂梅
一個有希望與信念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我想那便是新中 國成立不久之時,每一個年輕人朝氣蓬勃的笑容與一身正義凜然的氣息。
張桂梅便是趕上了那個人人都在喊口號的全新時代。
那時的她臉上還沒有樹皮般的皺紋,嘴角微微揚起的笑容燦爛真誠,紅彤彤的臉頰是青春獨有的符號,身着漂亮的長裙,留着清爽的短髮,大步走向美好的未來。

1974年,17歲的張桂梅離開了黑龍家的家,積極響應着國家“三線建設”的政策,和自己的姐姐告別了年邁體弱的父親與已經逝去的母親,踏上了去往雲南省邊疆建設的道路。
在林場的炊事班中,張桂梅並沒有展現出家庭小女兒身份下應有的“嬌氣”,反倒是憑藉優秀的廚藝、地道的東北菜狠狠地征服了大夥的胃,也正因其出色的工作效率,不到一年的時間她就被調到了另一個林場做黨校任團支部書記的工作。

信仰可以讓一個人不懼苦難不怕生死,而張桂梅似乎早在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覺悟了,不論是多麼艱苦的生活條件都沒有阻擋她追隨dang的腳步,緊接着張桂梅所接觸的職位越來越多,先是在林業局機關做文書工作,後又成爲了婦女主任深入民生調查,直到1983年一個如意郎君的出現,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林業局子弟學校的校長董玉漢安靜的不像是那個年代的人,他總是熱衷於思考,性格內向,將所有的小情緒都藏在心裏,而顛沛流離的張桂梅則似有若無的對這種“特別”產生了情愫。

張桂梅丈夫
那段時間她終於在子弟學校穩定了下來,接觸的不是紙墨的政治工作,而是一羣稚嫩可愛的孩子,教書育人的工作不光讓她得以明白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也昇華了張桂梅的靈魂,她既是老師,也是一個虔誠的學生。
1988年,張桂梅以極爲亮眼的成績考進了麗江教育學院,在這之前她早已收穫一段常人嚮往的愛情,兩個知識份子的情投意合爲生活帶來了一點不同於往日的暖意,於是畢業後這對小情侶與大多人一樣馬不停蹄的在大理市定居,並結爲了夫妻。

那個夢寐以求的家庭是張桂梅一生中爲數不多稱得上物質富有的時光,來之不易的幸福在尚未發展成熟的中國是一種奢求。
可命運卻偏偏不放過普通人。
1995年,丈夫得癌症的消息擊碎了張桂梅的精神支柱,她掏空家底,花光了所有的積蓄,卻依然拼不過死神的點名鋪。
她似乎又回到了最迷茫的時候,人人都能看到的結局近在眼前,可她不服氣,砸鍋賣鐵都要度過這劫。
終於,丈夫董玉漢似乎對張桂梅產生了歉意,他離開了。
一個親近的人從確診到死亡不過是一張白紙黑字的名單,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浪花般在張桂梅眼前翻湧。
一個想法頓時湧上心頭,“人爲什麼活着?”
帶着悲傷的情緒與一個沉重的話題,她逃離了大理市,來到了偏遠山區的麗江市華坪縣中心學校,是一次逃避現實的不二之選,更是一次正視自我的哲學追問。

爲了讓自己從情緒中剝離,她主動要求帶四個班級的課程,其中還包括初三畢業班,或許在忙碌中無暇思念,或是在悲痛中“懲罰”自己。

——消失的女孩
一段新生活的征途總是伴隨着些許的不確定性,而一個如胎兒般碩大的腫瘤,則是張桂梅不幸生活的開端。
在拿到確診通知書時她先是驚訝,隨後快速回頭看向了步步緊逼的中考,那聲音如雷貫耳,在張桂梅的腦海中不斷翻湧,甚至那龐然巨物的威脅大過了腫瘤的隱隱作痛。
“大山裏的孩子想要走出去太難了。”
一次中考對於普通人來說可能意味着是人生的選擇,而對於山裏人來講,那是他們能否正常生活的條件,是一次機不可失的必須。
作爲老師,張桂梅深知臨近中考更替老師會爲學生帶來怎樣的壓力,那時她似乎突然理解了活着的意義,抽屜一開就將病例鎖了進去 ,隨後用東北話的灑脫,回贈了病魔的威脅。

“乾脆豁出去了,死就死,活就活,我就把它(病歷)鎖到抽屜裏去!”
長達數月的時間裏,張桂梅像是忘記了那顆腫瘤似的,她的眼裏是一羣與命運抗爭的孩子,是不服命的抵抗,身爲教師的使命感一直支撐她走到了七月,待目送了最後一個孩子進入考場後,張桂梅才心安理得的去醫院做手術。
但很快張桂梅就意識到養尊處優的生活並不適合她,事實上從丈夫逝去之後,她就找到了自我救贖之地,“人爲什麼要活着?”的問題並不難回答,“活着要做什麼?”纔是重中之重,而張桂梅已經認清了自己的使命,那是黨性光輝的閃耀,是她身爲人民教師的責任與擔當,是負責歷史接力棒的傳承。

她草草結束了一個月的臥牀期,不顧醫生的勸阻再一次返回了崗位,並且更加關照山區的孩子們。
在任職期間她看到了太多的貧困,山裏老一輩的人爭先恐後的送孩子來上學,最後卻又因爲褲兜裏零散的硬幣而小心翼翼的離去,坐在校外扎着小辮的女孩,雙眼放光雙手拖着下巴,待人潮洶湧之際又黯然失色,她的命運肉眼可見的清晰,是矜矜業業的家庭主婦,是不帶情感的利益出嫁,總之她是山的一角無法割離。

每當見到這種情況發生,張桂梅都會陷入一種深深地無力感當中,哪怕她勤勞節約,僅用三元解決日常,向因學費而低頭沉默的家長積極伸出援手,也永遠無法填飽骨瘦嶙峋的人們,她知道這羣孩子面臨的是更深層次的困難,不只是金錢那麼簡單。
直到幾次的家庭訪談終於讓她找到了根源,那是幾個消失的女孩。

臨近高考的缺席最爲致命,張桂梅跋山涉水,走二十多里路攀上了山峯,幾個小屋子呈圓形排布屹立在不遠處,像是一座層巒疊嶂的監獄。
走進學生的家裏總是那麼似曾相處,一個苟着脊背的男人亦或是一個滿不在乎的女人,起初當問起退學原因時張桂梅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沒想到的是一位母親的話卻讓她憤怒到瞠目結舌。
“我的兒子要上學。”
“你女兒都高三了你兒子才初二啊?要高考了啊?”
“可是他是兒子。”
那刻,所有的窮苦都抵不過一句偏見,所有的怒火都不過是沉默之後的震耳欲聾。
她想要反駁什麼,卻只能無濟於事,張桂梅與眼前瘦弱母親的體型近乎一致,那是終日鹹菜腐乳的代價。
“是什麼區分了我們?”
一個偉大理想的種子就此埋下。


——尋找女孩
張桂梅的病痛愈發頻率,只因她更加頻繁的站在講臺,哪怕暈倒住院之時,她醒來的第一句話也還是關乎自己的學生。
縣裏的人得知張桂梅的病情後便紛紛出來捐錢爲她治病,一些人身上僅有幾塊的路費也毫不猶豫的貢獻了出來,就連縣長也熱淚盈眶的對張桂梅說
“張老師你不要怕,就算我們再窮也要救活你!”
說到這裏,張桂梅在後來的採訪中第一次留下了眼淚。
“他們那麼不要命的救我,我因爲他們活過來了,我一定要爲這裏做點什麼。”

早在募捐之前,張桂梅就在兼任新建的華坪縣兒童福利院時發現了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如果說“重男輕女”的思想影響了男女上學比例的失調,那麼其根深蒂固的偏見,則是直接扼殺了許多女性的人生。
孤兒院的女孩普遍與學校呈現反面比例,少數的男孩大多都是因父母雙亡而無可奈何的成爲遺孤,而大多數女孩卻幾乎都是由於家庭負擔亦或是性別錯誤而被迫流入。
這近乎是一個無法解決的惡性循環,低素質母親教育出低素質女兒,低素質女兒再生出低素質孫女,自然這些女孩的命運也是如出一轍的悲慘。

她們從小不是男性的附庸品就是父母意外之下的犧牲品,即使張桂梅已經拼全力與看不到頭的大山搶人,即使她深刻關愛着這羣孤兒,已經成爲了他們的媽媽,但卻終究無法拔出封建思想的惡根。
因爲被搶走的女孩總會“懂事”的哭喊着“不想上”,家長的眼眼神總是如此漠視,孤兒院的女孩數量也是隻增不減,她總有一天會先行一步離開,那時這羣可憐的孩子又該從哪裏獲得愛呢?
“帶走一個...再帶走一個”

她像是《血戰鋼鋸嶺》的戴斯蒙德,近乎着魔般的尋找“消失的女孩”,以至於敞亮的大路與鄰居的家裏總能見到一位老師在與女孩的父母發生爭執,那無知、蹉跎、井底之蛙的一生,那出生、生子、耕地、老去的循規蹈矩,那一眼望得到頭的窮途末路。張桂梅不願眼睜睜的看着這羣女孩的人生被葬送,又再一次回到了丈夫癌症之時的急迫,砸鍋賣鐵也要救...
但這一次她不再迷茫,那顆種子生根發芽得以重現,張桂梅要在煙霧繚繞的山裏點一盞燈,一盞足矣照亮所有女孩道路的燈。


——困難重重的女子高中
女子高中的理想看似簡單,實行起來卻無比困難,首先是資金問題,張桂梅的想法是女子高中的所有女孩必須能免費讀書,即使用掉了之前縣城捐款的手術費也遠遠不夠。
於是2005年前後總能看見張桂梅帶着自己的榮譽證書下山“化緣”,她依然帶着年輕時的朝氣蓬勃,慈祥的笑容多了些褶皺卻依舊真誠。
“幫幫忙嘛...多少錢都可以。”

然而輕聲細語的求助換來的不是智商的質疑,就是“騙子”的辱罵,唾沫與鼻涕接連不斷的湧現,放狗咬人的事件層出不窮,漸漸的她的腳上多了些傷痕,臉上多了絲憂愁,卻好似一個看淡風雲的老人,於莫虛烏有的罵名中隱入塵煙,又不肯放棄。
在大山裏建免費女高的想法即使放到今天也很少會有人相信,爲了女孩們的人生她付出了太多,甚至錯過了與自己臨死的哥哥見面的機會。
那是一次北京企業家的募捐活動,東北的哥哥重病在牀,心想最後能見到妹妹張桂梅一面。
可她知道,這次不去下次就很難有募捐的機會了,沒人能理解她當時的心情,只剩下哥哥沉重的呼吸聲逐漸減緩,直到眼前的張桂梅停留在了十七歲遠走他鄉的那一刻。
待張桂梅再一次撥通家裏的電話時,她迎接的是另一個親近的人逝去。

幾年過後,僅一萬多元的捐款也開始讓張桂梅心中的理想動搖,她從不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爲,只是感覺辜負了縣裏的期盼,正當所有人都一籌莫展之際,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露面,成就了那個遙不可及的理想。
2007年的網絡剛剛興起,張桂梅被選爲了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她用那時所贈與的獎金買了一臺筆記本電腦,在狹小的屏幕內寫下了一篇裝滿世界的文章,名字就叫做《我有一個夢想》。

常年在山中奔波的生活讓她的褲子多了些破洞,而恰恰也是張桂梅節衣縮食的習慣,得到了一個女記者的青睞,終於這風吹雨打的募捐生活走到了頭,縣外的人也通過文章的採訪,看到了這樣一位偉大的校長,各地政府都紛紛參與到了這場”拯救大山女孩“的行動中,一百萬元的經費讓這個夢想的帆船得以啓航。
2008年8月,中 國第一所真正意義的免費女子高中塵埃落定,首批被送入讀書的一百個山村女孩第一次看見了自己明朗的未來。
但即使最關鍵的經費問題解決了,長線的素質教育卻並沒有張桂梅所想象的那麼容易。

在剛開學不久,張桂梅就發現了第一個難題,學生的基礎文化水平太差了,有些甚至得從小學交起,分班也是個麻煩事,她左思右想,最終還是選擇了爭議聲較大的軍事化管理,並且要求所有教職工全年無休,學生早上五點起牀,晚上十二點後下課,唯一的休息時間也僅限於午飯的十分鐘與周天的三個小時。

如此艱苦的學習環境自然趕走了一大批教師,首批17名教職員工相繼辭職最後只剩下了8名,而最令張桂梅在意的,反倒是離校的六個學生,她再一次挨家挨戶的上門,身體素質的日漸下降與病痛使她寸步難行,那條通往小村的小道上總能看見張桂梅步履蹣跚的痕跡,可最終由於衆所周知的緣故,她只帶回來了兩名學生。
”一定要讓孩子們唸書,我們不收一分錢,一百個孩子一個不落。“
這句話張桂梅已經不知道說了多少遍,事到如今她也只有一股腦的向前,可六名老師哪夠九十六個學生的不間斷授課啊,哪怕張桂梅不喫不喝的站上一天,也無法教授其餘課程的知識。

爲數不多的八名老師也開始打了退堂鼓,一些人提議送一些女娃去縣高中上學,政府肯定也會承諾免費,張桂梅眼睛眨了眨,她知道縣裏高中不論是生活水平還是教育質量都會比現在高一點,但就像女高創立的初衷一樣,山裏的孩子不喫苦不可能走的出大山。
心灰意冷的張桂梅收拾起了教師們的資料,經歷了神性的捨生取義與人性的理想主義,女高這條路似乎要走到頭了,直到一道信仰的光芒落下,打在張桂梅瘦小的身上。
那是六個教職工dang員的身份爲她帶來的希望。
一個高尚的靈魂必然會有一個堅強的信仰伴其左右。
張桂梅將六個dang員教師集中起來,絡繹不絕的說道

“假如在戰爭年代,這個陣地上只有一個dang員,這個陣地都不會丟掉,我們剩六個dang員,我們把這塊扶貧的陣地給dang丟掉,你們說怎麼辦吧。”
老師們紛紛低下了頭。
在回想起這一幕時,紀錄片裏的張桂梅再一次梗塞,幾個老師滿臉淚花,他們有着共同的信仰,自然也會有無窮的力量。
就這樣,幾人在課程上輪番上陣,老師也常常以身作則的陪着學生到凌晨,學生上廁所時總有兩個老師跟隨以防野生動物的襲擊,張桂梅自己則每天習以爲常的早起,爲睏意襲捲的孩子們點亮明燈。
“姑娘們,起牀了!”

晨跑的時候,張桂梅也總是拿起話筒響亮又親切的大喊
“傻丫頭,快點唄!都是年輕女娃娃!”
那段時間,全校都能聽到張桂梅洪亮的嗓門,你從她的身上看不出一點病危的痕跡,有的只是一個心懷信念的校長樹立校風,是一個認真負責的老師教書育人,是一個勤勞樸實的保安保衛安全,是一個炊事班的阿姨噓寒問暖。
第一批女子高中學生進入考場的那年,百分百上線率的成績讓所有人都興奮不已,那是山裏女孩們終於能掌控命運的證明,是所有人一同努力至今的成果,她們生來本就沒有踏上起跑線的資格,而張桂梅則用盡全力,爲其拉出了一條衝破命運枷鎖的終點線。

——質疑從未停止,她的一生無需解釋
她們是醫生,她們是警察,她們是律師,她們是教師。
而張桂梅則一期又一期的目送那些苦命的孩子們遠去,對她來講,今天多送走了一個人就是拯救了三代,她們會有自己的女兒,那些女孩生活在城市裏,而非山中之籠。
山裏本無花草,張桂梅行萬里路,坊千餘人,灑下了希望的種子,即使這代價是疾病纏身,即使是窮盡一生的酸苦,她還是與年輕時的自己一致,朝氣蓬勃,眼裏帶光,可能這便是信仰的力量吧。

很長一段時間,張桂梅的教育理念與對”家庭主婦“的言論都受到各方勢力的抨擊,以新時代”覺醒“青年的那一方認爲這種教育是舊時代的遺留產物,以”覺醒爲主的部分極端女quan則認爲女性不應該被定義,她們想做家庭主婦就做家庭主婦,而現如今還會有些非蠢即壞的人說“女校搶佔了男方資源”,但他們,或者說是我們大多數普通人本就沒有資格去對張桂梅校長的作爲指指點點,她口中的“家庭主婦”並非是指城裏人的家庭主婦,而是她們努力了這麼久讓女孩擁有選擇的機會,卻還有從校內出去的女孩會選擇家庭主婦這一農村男性附庸品的職業,這令她感到寒心,而那魔鬼般的教育制度如果不魔鬼,也就沒有那麼多女孩能走出大山。

在紀錄片中,張桂梅的三次落淚全部來源於信仰的感動,第一滴淚是縣城人信仰的捐款,第二滴淚是dang員責任的宣誓,第三滴淚是她送出去的學生們心中也有了信仰,是guo家的信仰。
張桂梅一生都在用行動去奉行那幾句詩詞
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於羣峯之巔俯視平庸的溝壑。我生來就是人傑而非草芥,我站在偉人之肩藐視卑微的懦夫!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