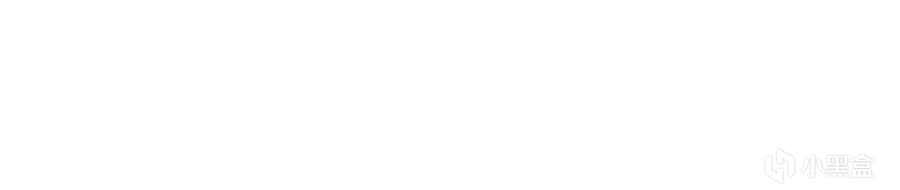
看完一場抽象直播之後,我被一把椅子跟蹤了。
1
我把筷子叼在嘴裏,騰出右手抓起鼠標,把同事剛剛發來的鏈接打開。屏幕上自動跳轉出設計簡潔的直播平臺頁面,一面碩大的黑屏佔據了核心空間,右側的彈幕欄裏不斷刷新着信息,什麼“搞快點”、“要開始了”、“首刷打卡”、“慕名而來”……
我從嘴裏取下筷子,打開外賣餐盒,邊喫邊等待直播開始。
直播間的標題取得有些隱晦——空無椅物,很明顯是在玩諧音梗。
現在的直播想要快速吸粉,多少都得搞點新花樣,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了。我之前並沒有看直播的習慣,今天純粹是受同事蠱惑,順便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看看所謂當下最火的直播,到底會玩出什麼新花樣來。
正當我琢磨的時候,直播間的黑屏先是抖動了一下,接着轉爲明亮,就像是攝像機上的黑布終於被人拿掉,鏡頭稍稍模糊了一陣子,但很快就完成了自行對焦。
直播的畫面非常簡單。固定機位下,鏡頭內拍攝到的是一個十分破舊的房間一角,說是一角,實際上鏡頭正對着一面牆,距離牆面大概有五六米,畫面邊緣處有些許環境光的痕跡,估計在鏡頭之外一定有窗戶。
那面牆髒兮兮的,基本看不出原本的顏色,經過長久的灰塵侵染又缺乏保養,一些地方的牆皮早已龜裂,能看到些許曾被水浸過的痕跡,還殘留着一些塗抹與刻劃,乍看上去像是一個被廢棄許久、爲拾荒者和孩童肆意摧殘的舊屋。房間裏遺落着許多垃圾和枯黃落葉,地板佈滿灰塵,拼接處露出微小的裂痕,有些邊緣已經開始翹起。
攝像機一動不動地呈現着這幅悽慘荒敗的景象,沒有任何批判或品論的意味,只是誠實地在向所有觀看者展現這一現實。但如果只是如此,倒算不上稀奇,也不具備爆火的特質,這畫面中點睛的,還是那把紅色椅子。
那是一把嶄新的紅色椅子,安靜地放置在殘破的房間中,靠着髒兮兮的牆壁,立於被灰塵垃圾覆蓋的地面之上。它無聲無息,和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卻又顯得相當協調,彷彿是某位先鋒藝術家精心設計出的一幅場景。紅椅子正對着鏡頭,椅中空無一物。
直播開啓的那一刻,右側的彈幕區也炸了鍋,表情和語氣詞瞬間將彈幕區淹沒,但這種盛況也就持續了幾分鐘,之後老觀衆們便紛紛開始給新觀衆們介紹起這個直播間的奇妙之處。
我一條條看過去,很快就明白了這個直播間的花樣。
說白了,這就是個盲盒。
直播內容就是破房間裏的一把紅色椅子,但是如果你看的時間足夠長,每天都會有不同的事物進入到鏡頭中,有時是一隻貓,有時是一隻鳥,有時是一個看不清長相的人,有時會在椅子上放一幅畫,或者擺放另一把椅子。雖然直播場景不變,但是始終會有不同的變量進入到畫面中,激發微妙的化學反應。
而在彈幕交流中,我發現那些老觀衆都在反覆討論一件事:同一天的直播裏,有些人看到的變量事物和其他人不一樣。
就爲這件事,不少老粉始終在爭吵,都認爲自己看到的纔是對的。
我覺得這可能是運用了某種串流技術,或者有人混進彈幕區裏刻意製造曼德拉效應,自然,這也不失爲一種宣傳手段。看膩了彈幕區裏不斷刷新的文字,我把視線重新放回到直播畫面裏,依舊是那把紅色椅子,十幾分鍾過去了,一切照舊。
這裏甚至沒有房管暗示刷禮物,大概主播並不指望能從中獲利。
喫完了外賣,我看到直播畫面裏依舊沒有變化,便關掉了網頁,抓起手機給同事發了條消息。
“看了,感覺也就那樣,沒什麼特別之處。”
幾分鐘後,同事回了我一個“笑哭”的表情。
我本以爲這事到此就結束了。
2
週一上午是部門例會時間,領導卻在會上扔給了我一個並不想接的任務——採訪“紅椅子”直播間的幕後團隊。
“首先,他們是有計劃地在統籌整個直播活動,從內容到形式、選題,場景佈置以及宣傳,這是個相當成熟的團隊在運作,一眼就能看出來。其次,直播的內容目前來看極具話題性,懂得利用觀衆的獵奇心理來吸引流量,這種做法很聰明。所以不管是誰在主導,他們的幕後故事都值得挖一挖。我已經找好了聯絡人,用了點關係,這個任務就交給你了,一定要寫篇漂亮的採訪稿出來。”
我面無表情地看着他說完這一大段自認理所當然的說辭,心裏卻泛起嘀咕。這也太巧了,前腳同事剛發給我紅椅子直播的鏈接,後腳領導就給了我採訪任務,我甚至有些懷疑他們是串通好了給我增加工作量。
“領導,我手裏還有一篇採訪正在寫,馬上就到截稿日期了……”
“往後延吧,那篇稿子不着急,你先把紅椅子的出了,要緊跟熱點,明白?”
領導絲毫沒有給我討價還價的餘地。我嘆了口氣,這場會議後面的內容我已經沒有心情聽下去了。
散會之後,我正在工位上寫策劃案,那位沒安好心的同事發來信息:
“怎麼樣?我讓你提前看眼直播沒錯吧?”
“滾,你小子肯定是把這活推到我頭上了。”我毫不客氣地回道。
“我是這種人嗎?傷心啊,這活我想接領導都不給。要不是你文案寫得好,這種時間緊任務重的工作,領導能放心交給你?”
“我懇求領導別放心我。插活這種事誰愛幹誰幹。”
“哎呀你這個格局……不扯了,等你和紅椅子團隊聊完了,記得給哥們兒透點內部消息,他們這個直播到底想達成什麼樣的目標,我挺好奇的。”
“好奇你自己去問啊。”
“你以爲我沒問過嗎?”
閒扯以同事的這句話做了結尾,更多的內情我沒有深追。畢竟在新媒體這個行業裏,每個編輯的眼睛都盯着最新最火的熱點,想必我這位同事是自己想追這個熱點,卻被領導潑了冷水,不敢直說吧。
下午領導就把採訪的相關資料單發給了我,並附了一條備註。
直接聯繫就行,其他的我都溝通好了。
我看着這條備註一頭霧水,似乎領導和這個團隊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難道是對方想借助這篇報道給自己引流?藉助新媒體增加曝光率,這種操作不是什麼新鮮事,可它不過是個獵奇的直播間,這樣做有必要嗎?
我打通了聯繫人的電話,主動報上自己的姓名和單位,簡要說明了聯繫的目的。
電話那邊非常安靜地聽我完,沉默片刻,然後嗯了一聲。
“那,採訪安排的話,您看本週內什麼時間合適?”
又是一陣沉默。
“週三,下午,兩點三十。”對方用一種平靜地,毫無感情的聲音說道,“地址我稍後發你。”
“好的好的,感謝。”
“請一個人來。”對方忽然說道。
“一個人?”
“對,這是已經約定好的。你一個人來。一個人採訪。”
“啊,行。可以,沒問題。”
“嗯。”
說完,對方就把電話掛了。
我看着手機屏幕,突然覺得有種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感覺。
3
爲了在採訪前瞭解到更多的信息,我這幾天都泡在論壇和貼吧裏,蒐羅各種信息和評論,還看完了整場的直播內容。空無椅物的直播時間是每天下午1點到5點,按理說,這個時間段並不理想,畢竟是工作時間,只有不上班的觀衆纔可能進來看。
我看的這兩天裏,直播內容沒有任何變化,從始至終都只有那一把紅椅子立在畫面裏。我注意到有的評論說看到一個影子,或者是幾隻小蟲子,但我確實是什麼都沒看見。更令我在意的是,直播間的人氣比我上週看的時候又漲了差不多50%。
小衆而又獨特,不得不承認,空無椅物的直播確實有獨到之處。可這種明目張膽欺騙觀衆的方式,恐怕紅不了太久。做這個直播的團隊到底圖什麼呢?
這也是我準備問的第一個問題。
我在週三按約定的時間抵達了約定地點。這是市郊一處廢棄的房子,位於一個爛尾樓盤的邊緣。看上去已經至少十年沒有人住了。房子的外牆是那種紅磚砌成的樣式,或許早幾年還算流行,但現在看來簡直就是上個世紀的古董。
我沒有敲門,因爲門根本沒鎖,一推就開。我先在門口給受訪人發了條“我到了”的信息,對方很快就回了條“直接進”作爲答覆。
推門進去,地板上滿是灰塵和垃圾,牆面斑駁破舊,佈滿開裂的牆皮和污漬。房間不大,兩室一廳的結構,我走進去之後就看到其中一個小間裏放着明顯不合畫風的物件。
那是一套拍攝設備,相當專業的拍攝設備,安放在一間較爲寬敞的房間裏,正對着一面髒兮兮的牆和一把嶄新的紅色座椅。
我站在房間門口,看着這個熟悉的場景。心跳不自主加快了一個檔位。
“坐吧。”早已在房間裏等候的受訪人說道。
我仔細打量了一下這個瘦高的年輕人,他面無表情地坐在角落裏,伸手示意我坐到靠牆的那把紅椅子上。他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夾克衫,配了一條洗到有些褪色的牛仔褲,鞋子髒兮兮的,怕是在這房間裏呆久了的緣故。
“我是來採訪的,不是來面試的。”我尷尬地笑笑。誰會願意坐在那把紅椅子上?鬼知道那上面還坐過什麼。
“我知道。但這是採訪的一部分。”對方絲毫沒有讓步的意思。
我掃了眼房間,除了那把紅椅子和受訪者屁股下面的馬紮,確實再沒有能提供座椅功能的物件。
無奈之下,我只能挪到紅椅子邊上,彎腰看了看椅面的乾淨程度,用手掃了掃並不存在的灰塵,然後慢慢坐了上去。
“現在不會在直播吧?”我隨口一問,想緩解下自己的尷尬。
“當然。”對方說着,拖着馬紮坐到直播攝像機的後面。於是房間裏呈現出的場景變成了我作爲受訪者面對鏡頭,而對方兼顧了攝影師和記者的身份。
“什麼?我可沒同意上直播!”我從椅子上跳起來,離開鏡頭的畫面範圍。
“麻煩坐到座位上。這只是採訪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同意,那我無法接受採訪。”
“你……”我想不出除了髒話之外更恰當的回答,但顯然髒話並不適合在這種場合下使用。退一步講,領導還等我出採訪稿呢。
我回到椅子上坐下,開啓錄音筆。
“可以開始了嗎?”我努力試圖讓自己的語氣和善一些。
“還有一件事。”對方說着,拿出一個平板電腦,把屏幕轉向我。
屏幕上是熟悉的直播間場景,如他所說,直播已經開始,骯髒的房間裏,一把乾淨的紅椅子,但是那椅子上是空的。
“這是什麼意思?”
“只是想讓你對現狀有一個瞭解。”對方說。他把平板放在一個支架上,屏幕始終對着我。畫面裏只有房間中的椅子,沒有人。
“所以說,有兩個直播場景?你們會隨機切換來呈現不同的畫面?”
問題脫口而出,即便它並不是我準備問的第一個採訪問題。
“不是,場地只有一個,就是這裏。”
“這不是實時畫面?”
“是實時的,目前正在直播。”
說着,對方拋來一個紙團。我看到平板畫面裏一個紙團突然飛入,打在牆上後又落在地面,滾出畫面。直播間裏也驀然刷出一波彈幕。
“我不明白。”
“那就問好了。”對方說,“可以問任何問題。”
4
你看直播嗎?
答案一般是看,或者不看。當然,也有人會答出偶爾看、有時看,喫飯時看這樣更爲具體的回答,但這也歸屬於看的範疇。說到底,這就是一個0或1的問題。
可你爲什麼要看直播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多到無以計數,但請允許我用一個簡單的、過於粗暴的答案來概括:因爲想看。
這是由千百萬直播觀衆的自由意志書寫而成的、最爲簡單樸素的答案。就像在晴朗的天氣裏抬頭看雲、看山一樣,它在那裏,而我想看看。
爲了響應這一訴求,我架起攝像機,對焦好鏡頭,在取景框中錨定我需要呈現的畫面,確認網絡頻道的暢通,以及其他直播時需準備的一切物件。萬事俱備,我開啓機器,接通連線,屬於我的直播就這樣開始了。
你知道什麼是直播的本質嗎?
就是我在鏡頭前講述一個故事,而你相信我所講的一切,併爲此花費金錢延續我所講述的一切。你甚至可以認爲這是一場現實主義戲劇,你我都是表演者,攝像機和屏幕是觀衆。
所以我想講的故事是這樣的:
在一座陳舊破敗的屋子裏,放着一把嶄新的紅椅子。
但是這個故事過於單調了。單調的場景,單調的空間,單調的釋放點,什麼都沒有,這隻能算得上是一個置景。不過沒有關係,它就是我要講的故事,這個故事從沒被他人講過,我是唯一的講述者,你只能選擇聽或是不聽。
人都是好奇的,也多少是從衆的,因此我從不缺觀衆,他們想看的當然不是一把椅子,他們想看的是變化,是未知的變數,是活生生的盲盒。
今天的盲盒裏會開出什麼?我自己也不清楚。這是一個謎題,對我對你都是如此。
而我現在要做的,是解開這個盲盒裏的機關,袒露出它裏面的設計原理。
你瞧,這個故事的核心是一把紅椅子,但不是隨便一把紅椅子,而是這把紅椅子。燈芯絨布料,銅質椅腿和椅背骨架,充填海綿彈性適中,這些共同組成了“這把”紅椅子。
但更爲重要的是坐在椅子裏的東西。它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個物件。
一個蘋果放在椅子上,屏幕裏能看到一本物理科普書籍;一杯水放在椅子上,屏幕裏出現的是一把雨傘;我自己坐在上面,屏幕裏出現的是一捆麻繩,諸如此類。
當然,我在直播間裏看到的物品種類更多。一隻貓,一條魚,一個盆栽,一件衣服,有觀衆留言說他記錄下了每一次出現的物品,試圖分析某種規律,但我想他不會得到任何有意義的結果。
所以,我想你多少明白了吧?這個椅子的詭異所在,就是將不同的東西放進去,在旁觀者眼中卻會看到與本體不同的、千奇百怪的內容。這就是直播的樂趣。
起初我也不信,直到我真的見到了結果。這把椅子應該被更多人看到,它也想要被更多人看到。你們會和我一樣看到這把椅子所呈現的奇觀,然後在日常中不斷地回憶它、討論它、記住它、關注它。然後,它也就這樣和你們建立了聯繫。
古人講非禮勿視,可如今只要又噱頭,不合禮又能怎樣?我只是用這把椅子爲觀衆們呈現一種新的娛樂,大家兩全其美,這難道不好嗎?
記者小哥,這就是我最誠懇的回答。
5
採訪花的時間比我預想中要長,當我從那間破舊的房子出來時,外面已經是華燈初上。雖然是臨近初夏的夜晚,但我依舊覺得有些渾身發冷。
受訪者對我的每個問題都事無鉅細地給出了回答,開設直播間的動機,對於直播主題的構思,想要表達的內容,後續的直播計劃等等,他每個問題都講的很慢,講的很小心,有種精心排練過的感覺。
想想看,一把紅椅子,上面無論放什麼東西,在攝像機裏都會看到不一樣的,這種手法確實有點巧思在裏面,就連直播者自己都信以爲真。
“這樣的直播,您覺得它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又想起自己的最後一個問題。
對方想了想,然後開口:
“作爲直播觀衆,他們想從直播中獲得什麼?是直播提供什麼就看什麼呢,還是因爲想要了解而去觀看?一個人的視野終歸是有限的,但通過直播,人們能夠看到不一樣的世界,能借助他人的視角去觀察世界另一面的風景,這原本是好的。但是,若有人爲了吸引觀衆,不斷以刻意的方式製造娛樂、追逐熱點,反而有點本末倒置。我想,空無椅物的直播更多是一種反省——除了椅子,你還能看到什麼?”
答案是,我什麼都看不到。
結束採訪後,我又花了不少時間,將各種東西放在紅椅子上,再從顯示器裏觀察,確實如對方所說,基本上椅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次,當我把揹包放在椅子上的時候,顯示器裏出現了一紮花束——新鮮的香檳玫瑰,用淡藍色的歐亞紙包成精緻的造型。
我不懂這些直播裏的奇技淫巧,但是我絕不可能在報道里寫怪力亂神,不然恐怕又要給這直播間帶來一波熱度,我的主編估計也會先讓我去洗洗腦子,然後寫點實際的內容出來,而不是去譁衆取寵。
我攔了輛出租,在車上整理起採訪稿的大綱,等回到住處的時候,我在樓下的便利店裏買了兩罐咖啡和一罐紅牛,踏着沉重的步伐準備迎接熬夜。
6
稿子寫的很順,半夜2點就搞完了。檢查了三遍保存狀態後,我合上電腦滾去睡覺,再睜眼已經是早上七點四十。
到公司把稿子交上去差不多半小時後,領導回覆了一個“好”字就沒了下文,我也沒再追問,拾起寫到一半的上一篇採訪稿繼續碼字,沒想到下午四點多接到了領導發來的信息。
我一頭霧水地敲門進去,屋裏除了領導,還坐着一個體型微胖的中年男人。
“坐。這位是……第三方機構的人,需要向你詢問一些情況,你配合就行。”領導囑咐一句後就不再開口,靠着椅背小口抿茶。
那個人遞給我一張照片。
“這個人見過嗎?”
照片裏是我昨天採訪的那個人,空無椅物的直播人。
“麻煩說一下你昨天和他見面的經過,越詳細越好。”中年男人說。
我想了想,把昨天整個採訪過程大致講了一遍。
“當時對方有什麼異常的表現嗎?”對方追問道。
“沒,就是個普通人。”
“你有事先了解過這個人的情況嗎?或者在採訪結束後?”他接着問道。
“沒有,我採訪的核心只是他的直播內容。”
“所以你沒有問過他的直播目的是什麼?”
“問了,他說就是想看看觀衆的反應,嘗試一下這種新奇的直播方式會不會被接受,還有什麼非禮勿視之類的。”
男人拿出筆記本寫下幾筆。
“有什麼問題嗎?他的直播又不犯法。”
“直播自殺可是會的。”男人說道。
“自殺?”
“這是昨天晚上的直播錄屏。”
男人遞來一個平板,屏幕裏還是熟悉的場景。點開播放後,視頻保持了大約兩分鐘的平靜,接着,突然在畫面的正上方掉下半個身子,懸在空中來回搖盪,因爲只有下半身在畫面裏,因此分不清是惡作劇還是真實情況。這個畫面只出現了10秒左右就被掐斷了。
“直播平臺識別到畫面異常後,迅速斷掉了直播間信號,有網友報了警,現場確認的結果是,這個人確實是在直播間裏上吊了。根據時間推算,以及現場的痕跡,你是他死前見的最後一個人,所以,你確定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異常嗎?”
我在腦子裏又過了一遍昨晚的經歷,受訪者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表情和動作,我確實都沒察覺到任何不對勁的地方。就算有,也只是他對直播一把紅椅子這件事的莫名執着。
我把這些和這個男人全部講了一遍。他默默聽完,不時微微點頭。
“稿子我看了。看樣子你加了不少潤色在裏面。”中年人說道,此時領導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陣子,“按你這個寫法,發出去後估計直播間的人數會再長一波,是他讓你這麼寫的嗎?”
“不是,我是隻有這麼寫,纔能有內容。按他自己的那套說辭,這直播從頭到尾都是個騙局,那些看直播的人都是他的試驗品,這種觀點發出來,會形成什麼樣的輿論,讀者反響會是什麼樣子,誰都不好說。搞不好我們公衆號也會受牽連,影響關注度,我這只是比較溫和的寫法,誰都不得罪。”
“對方知道你要這麼寫嗎?”
“我臨走時提到過,這也是流程之一,我得告知被訪者具體的主題方向,以防對方有不同意見。他沒說這樣寫不行。”
中年人不說話了,低下頭開始思考。
“要知道,你不是第一個採訪他的人。”半響後,中年人抬起頭說,“但之前的採訪稿無一例外地都沒發出去。原因很簡單,關於這把紅椅子的事,並非只有直播裏看到的那麼簡單。他也不是第一個因爲這把椅子送命的人。在他之前接觸過這把椅子的,最後也都選擇了自我了斷。”
“爲什麼?”
“好問題,但是我建議你還是不要深究了。你現在需要的是給自己放個假,並且忘掉那把該死的椅子。明白?”
這次意外的談話就此結束,中年男人和主編說了兩句後便匆匆離開,只剩下我和主編在辦公室裏陷入沉默。
“採訪稿應該是上不了了吧?”我小聲地問了一句。
主編嘆了口氣。
“這次辛苦你了,如果想休假,可以批你三天。”主編說完瞄了我一眼,“你的上一篇稿子今天能搞完嘛?”
“差不多。”
“完了就發我,然後回去休息三天吧,算到年假裏。別再想這事了。”
我點點頭。
7
如果這件事就此結束,我也沒必要把它寫下來。
在休假的幾天裏,我聯繫了一些朋友,拜託他們幫忙打聽那個自殺播主的背景信息,我總覺得一切沒那麼簡單。
沒有人會平白無故自殺,除非遭遇了重大變故、徹底喪失了活下去的動力。
然而。朋友發給我的信息卻比我想的更復雜。
這個自殺的播主原本有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並非依靠直播爲生。他幼年時父母離異,跟着奶奶長大,對老人感情很深。但在差不多兩年前,奶奶上了直播詐騙的當,把積蓄都賠了進去。播主當時立刻報警,但依舊沒能把錢要回來。氣急之下,播主揣了把刀在身上,找到直播平臺的負責人理論,兩人從爭吵上升到鬥毆。最終,法院判定播主有主觀犯罪嫌疑,以故意傷害判了他一年半的刑期以及大筆的賠償金。
播主的生活就這樣垮掉了。他所有的錢都抵了賠償款,服刑期間,播主的奶奶也因身體原因去世。這一系列的後果,讓博主從一個普通人徹底淪爲一個有案底的無家可歸者。當他服刑期滿離開監獄時,身無分文,無處可去。他也試過去打零工,找份穩定的工作,但是身上的案底註定讓他無法被平等對待。
直到有人介紹給他一份直播的工作,而直播的主角,竟然是一把椅子。
“這個團隊是什麼來頭?”
“不清楚,警方那邊聽說也在查,但是沒什麼頭緒。”
“還有別的情況嗎?”
“還有一個,那天那人找你們談話,有一個關鍵信息沒說。”
“什麼信息?”
“那把椅子沒了。”
我一時間沒聽明白。
“那把紅椅子當時被警察作爲證物拉回了局裏,一直放在證物倉庫,第二天再去就沒了,調監控也沒看到有人取走。基本上算是憑空消失。有傳言說那椅子不對勁,具體我也不清楚。總之就是這麼個狀況。他們現在還在找呢。”
掛了電話,我依舊一頭霧水,突兀的自殺,消失的椅子,一切都有點超現實的意味。
還好朋友的約飯電話打斷了我的無端猜想。我們幾人久違地喫了頓燒烤,喝完兩箱啤酒,在夜色溫良之際微醺着彼此告別。
我暈乎乎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到前方路邊有一個熟悉的物件。
那是一把紅色的椅子。有幾個年輕人正拿着手機對着它拍攝,還一臉興奮地對着屏幕說着什麼。
我走上前去,這才聽清了那幾個年輕人在說什麼。他們是空無椅物直播間的觀衆,無意間發現了這把椅子後,開始自主發起一場臨時直播。他們挨個坐在椅子上,讓同伴拍下自己的姿態,又將不同的東西放在椅子上,觀察屏幕裏的景象。
不過一切似乎沒有什麼神奇的地方,椅子上放什麼,屏幕裏就顯示什麼,看來直播間裏的神話並沒有被打破。
看到我走近,幾個年輕人便嬉笑着離去,留下我一人面對這把椅子。我默默地注視了一陣,幾乎可以肯定這就是那把椅子。可它爲何會出現在這裏?是誰把它擺在這的?我是不是該通知警察失物找到了?
猶豫之際,我不自覺地坐到這把椅子上,自然地就像某種條件反射。身體沉入椅子的那刻,我周圍的一切突然開始模糊、變化,恍惚間我覺得自己又回到了那天採訪的場景中。
一個身影在我前方不遠的地方站立,手中握着一捆麻繩。
“爲什麼自殺?”我問。
“我以爲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這把椅子。”一個聲音縹緲在我耳畔。
“擺脫?那只是一把椅子。”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椅子,你一旦坐上去,就會被纏上。它用噩夢折磨我,讓我就範,讓我將它展示給更多人,吸引更多人……”
“爲何不離開?”
“有什麼用呢?我拆過它,燒過它,扔進河裏。它總會回來……你會明白的。”
8
我再次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人在醫院裏。據醫生講,我昨晚被人發現坐在路邊的一個椅子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是被好心人打電話叫救護車拉到醫院搶救的。
醫生問了一圈我昨天喫過什麼東西,最後判斷我可能是食物中毒。
“到夏天了,食物容易變質,經過加工後更不容易被發現。不過人沒事就好,你今天下午就能出院了。”
醫生走後,我躺在牀上想昨晚的那個夢,我依稀記得有人對我說了什麼,但始終想不起那人的長相。
“你也是運氣好,被人及時發現,不然現在我們就要給你收屍了。”
來者的聲音嚇了我一跳,我從牀上差點滾下來,還好病牀的欄杆拒絕配合。
中年男人在病房門口打量着我,眼神裏帶着些許戲謔。
“你見到那把椅子了?”
我點點頭。
“以後陌生的椅子不要隨便坐,自己多長個心眼。”他說着,在我對面的牀鋪坐下。
“你到底是誰?”
男人笑笑,“你可以叫我穆先生。”
“我能給你的建議,就是別再想椅子了,把它忘掉,把那場採訪也忘掉,就當一切都沒發生過。那天你說到非禮勿視,其實沒錯,不合禮法的東西看多了自有壞處,不合自然規律的東西看多了也一樣。”
“我不明白。”
“沒關係,不需要明白。有時心願是會得到回應和滿足的,但是你不會知道回應和滿足你的是什麼。爲了搞清楚這個丟了命,不值得吧?”
我搖頭。
“別去想它,這是我唯一的忠告。”
“我儘量。”
“你得盡力。”他遞給我一張名片,“有任何需要,給我打電話。”
男人走後,我簡單收拾了一下東西,把住院費用結算清楚後,便走出了醫院。
今天的天氣很好,陽光晴朗,氣溫舒適,我餘光忽然瞥到路邊的一個東西,那是一把紅椅子,十分自然地被擺放在路旁,等待有人坐上去。我看了它兩眼,徑直往前走,把它甩在身後,順手掏出手機和那張名片。
此時,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我今後大概再也不會看直播了。
-END-
作者丨薊犁瘋狗
歡迎關注我們,
你愛看的奇聞、熱點、懸疑、腦洞都在這裏。
喜歡的話不如點個贊支持我們鴨
更多遊戲資訊請關註:電玩幫遊戲資訊專區
電玩幫圖文攻略 www.vgover.com
















